ة╛â╚╚▌╒ز╥زة┐ةة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îت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╡┌2┐ى╓▒╜╙h│²�����ثش▀@ءO╥╫▒╗└و╜ظئل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╒J╢ذء╦£╩┼c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╖╓╡└ôPكs�ةث╚╗╢°ثش╚ق╣√╪╡╫ْùë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╒J╢ذ╗∙£╩����ثش▓╗╡سـ■╩╩د┼╨¤ض╔╧╡─îثءI(yذذ)╨╘ةت╦╝┐╝╔╧╡─╜ؤإ·╨╘�ةت╫Cô■╔╧╡─┐╔▐DôQ╨╘╡╚╓T╢ضî╥µثش╢°╟╥ـ■▀M╢°ôpé√╖ذ╓╚╨ٌ╡─╜y╥╗╨╘┼c╚┌╪ئ╨╘����ةث╥ٌ┤╦ثش▓╗─▄îت▀@╥╗h│²└و╜ظئلة░╜^îخ▓╗─▄╥└╒╒ة▒�����ثش╢°ّز└و╜ظئلé╨╘ْهع^╡─╜ظ│²�ثش╞غ▓ت▓╗╖┴╡K╦╛╖ذ▓┘╫≈╓╨îخ╟░╓├╖ذء╦£╩╡─àت╒╒ثش╥ضئل╨╠╖ذ┌A╡├╧ضîخ╗»┼╨¤ض╡─┐╒لg�����ةث═شـrثششF╨╨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╔╧╦∙┤_┴ت╡─╝┘╦┼c┴╙╦â╔╖╓─ث╩╜��ثش╚╘╚╗┤µ╘┌╕┼─ى╕é║╧�����ةت╛▀ٍwى╨═╗ه═ش╡╚▒╫╢╦���ثش╨ك╥ز╘┌╠╪e╥(guذر)╖╢┼c╞╒═ذ╥(guذر)╖╢╡─╥ظ┴x╔╧╓╪╨┬î╥ـ║═╠└و��ث╗îخ╘ِ╘O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└و╜ظ���ثش╥▓╨ك╘┌╟░╓├╖ذ┼c▒ث╒╧╖ذ╡─àf═ش╥ظ┴x╔╧╝╙╥╘░╤╬╒ةث╘┌┤╦├}╜j╔╧����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îخ╝┘╦ةت┴╙╦╕┼─ى╡─╜Yءï╨╘╒{╒√�ثش╥╘╝░îت¤M╓╞╨═╝┘╦┼c┴╙╦╝╙╥╘âنx▓ت╓├╚ن╞غ╡┌124ùl╙ك╥╘╥(guذر)╓╞╡─╫ِ╖ذثش▌▒╪îد╓┬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�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╥(guذر)╓╞░ن╜╡─╩╒┐s��ثش╥▓▌▒╪╥ز╟ٍ├µ╧ٌ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╘O╓├╨┬╡─▒ث╒╧╨╘╥(guذر)╖╢����ةث▀@╒²╩╟╘ِ╘O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╕∙▒╛╙آCةث╢°إô▓╪╞غ║ٍ╡─╥(guذر)╖╢╥ظêD���ثشt╘┌╙┌╣س▒è╜ة┐╡╔·├ⁿ╖ذ╥µ┼c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╖ذ╥µ╡─╖╓نx┼c╝â╗»�����ةث╡س▀z║╢╡─╩╟�ثش▀@╥╗┼ش┴خنy╤╘│╔╣خ���ة���ث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╡─┴ت╖ذ╘O╢ذثش▓╗âH╩╣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╖ذ╥µ╖╓نx┼c╝â╗»╨د╣√اo╖ذ╘┌▒ث╒╧╖ذ╔╧╫°î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ـ■دو╛╓▓┐ٍw╧╡╬╔yةت╦╛╖ذ╒J╢ذ└دنy╡╚▒╫╢╦ةث═شـr����ثش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╥▓╬┤îخ▒╗âنx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╨╬│╔═م╒√╕▓╔wثش▀M╢°┐╔─▄╨╬│╔╨┬╡─╖ذ┬╔┬ر╢┤��ث╗▒╛┤╬╨▐╖ذ▀╨┬╘ِ┴╦îخ╣╩╥ظ╠ط╣ر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╨╨ئل╡─╠┴P�����ثش╩╣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╥(guذر)╓╞µ£ùl╧ٌ║ٍ╢╦╤╙╒╣����ثش╡س╚╘╬┤╨╬│╔╚س┴≈│╠�����ةتل]صh(huذتn)╩╜╡─╓▄╤╙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�ةثîخ┤╦â╔┐ى╥(guذر)╢ذ╢°╤╘ثش╚ق║╬└و╜ظة░├≈╓زة▒ة░╩╣╙├ة▒╝░╖╕╫ي╓≈ٍw╡╚ûى}�����ثش╚╘╚╗┤µ╘┌▀M╥╗▓╜│╬╟ف╡─╙ض╡╪ةث
ة╛مPµI╘~ة┐ةة╦╞╖╖╕╫يةة╝┘╦ةة┴╙╦ةة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ةة╣س▒è╜ة┐╡┼c╔·├ⁿ╖ذ╥µ
?
╘┌ç°╝╥╒√ٍw░▓╚س╙^╡─╙^╒╒╧┬����ثش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╠╪eمP╫تى^و¤░▓╚س��ةت│ِ╨╨░▓╚س║═╔ض╝ظ░▓╚س╡╚ىI╙ٌ╡─╨▐╖ذ���ةث╦╞╖░▓╚س╫≈ئل├ً╔·ىI╙ٌ╡─╓╪┤ٍمP╟╨��ثش╥▓وء▌│╔ئل▒╛┤╬╨╠╖ذ╨▐╒²╡─╓╪ⁿc╓«╥╗����ةث╞غ╓╨����ثش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╡─╡┌5ùlثذîخّزة╢╨╠╖ذة╖ ╡┌141ùlثرةت╡┌6ùlثذîخّز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ثر��ةت╡┌7ùlثذ╘ِ╘O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ثر║═╡┌39ùlثذîخّز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408ùl╓«╥╗ثر╔µ╝░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î╩ر┼c▒O(jiذةn)╣▄ûى}�ةث╙╔╙┌╡┌39ùl╩╟╘┌╩│╞╖▒O(jiذةn)╣▄ئ^┬أ╫ي╡─╗∙╡A╔╧╝╙╥╘╤a│غ╨▐╒²╡─ثش╘┌ٍw╧╡╬╗╓├���ةت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�����ةت╨╨ئل╓≈ٍw���ةت╨╨ئل╖╜╩╜╡╚╖╜├µ╛∙┼c╡┌5ùl���ةت╡┌6ùlةت╡┌7ùl┤µ╘┌ي@╓°à^(qذ▒)e��ثش╨كîث╬─┴و╒ô����ثش╣╩▒╛╬─╡─╙ّ╒ô╓╪╨─╘┌╡┌5ùlةت╡┌6ùl���ةت╡┌7ùl╓«╔╧�����ةث╛═▀@╥╗╥(guذر)╖╢╝»║╧╢°╤╘��ثش╞غ╓≈╥زç·└@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╡─╨▐╒²╒╣ل_�ثش▓╗╡س╘┌ٍw╧╡╬╗╓├╔╧┐┐╜ⁿ����ثش╘┌╨╨ئل╖╜╩╜╔╧ى╦╞ثش╢°╟╥╘┌╨╨ئل┐═ٍw╔╧┤µ╘┌╛o├▄╖╓╣ج��ثش╥ٌ╢°▀m║╧╫≈ئل╥╗é╥(guذر)╖╢╚║╝╙╥╘╙ّ╒ô��ةث
╛═╔╧╩ِâ╔é╖╕╫ي╢°╤╘�����ثش▒╛┤╬╡─╨╠╖ذ╨▐╒²╓≈╥ز╝»╓╨╘┌╥╘╧┬╦─ⁿcث║╞غ╥╗�����ثش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╒J╢ذء╦£╩┼c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├ôع^ةث╥ض╝┤����ثشh│²┴╦ة░▒╛ùl╦∙╖Q╝┘╦���ثش╩╟╓╕╥└╒╒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╥(guذر)╢ذî┘╙┌╝┘╦║═░┤╝┘╦╠└و╡─╦╞╖ةت╖╟╦╞╖ة▒���ثش┴╙╦═ش╔╧���ةث╞غ╢■ثش┼c╔╧ⁿc╧ض▀B���ثش╕ⁿ╝╙╫ت╓╪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╡─╖╓┴ت┼c╝â╗»��ةث╥▓╝┤��ثش═ذ▀^╘ِ╘O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����ثشîت╬╝â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╨ئل�ثش░ⁿ└ذ╘ص╧╚╘┌¤M╓╞╨═╝┘╦ةت┴╙╦╓╨╦∙╥(guذر)╓╞╡─▓┐╖╓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╖╓نx│ِو▓ت╬┴╨╠└و�ةث╞غ╚²ثش╥(guذر)╓╞╡─╨╨ئلى╨═┼c╨╨ئلµ£ùl╙╨╦∙═╪╒╣���ةث╘ص╧╚���ثش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╦∙╥(guذر)╓╞╡─╨╨ئلى╨═╝»╓╨╘┌╔·«a║═غN╩█â╔╖N╨╨ئلثش▒╛┤╬╨▐╒²╘ِ╝╙┴╦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╢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ة▒�ةث═شـrثش╘┌╘ِ╘O╡─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╓╨�����ثش╥▓îخ╦╞╖╔م╒ê╫تâ╘╓╨╡─╞█ٌ_╨╨ئل╝╙╥╘╤a│غ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ةث╥╘╔╧╫â╗»ثش▓╗âH╩╣▒╗╥(guذر)╓╞╨╨ئل╡─ى╨═╙╨╦∙╘ِ╝╙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─╥(guذر)╓╞╡─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╗ٌµ£ùl╔╧╙^▓هثش╥▓─╔·«a���ةتغN╩█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▀M╥╗▓╜═╪╒╣╡╜╟░╢╦╡─╔م╒ê╫تâ╘║═║ٍ╢╦╡─╩╣╙├╨╨ئل�ثش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╕ⁿئل╓▄╤╙║╧└وةث╞غ╦─����ثش╖ذ╢ذ╨╠╡─╒{╒√ةث╓≈╥زٍwشF╘┌╡┌142ùl╓╨╡─┴P╜≡╨╠╘O╓├─▒╢▒╚╓╞╕─ئلاo╧▐ى~╓╞�ثش╝┤╙╔ة░▓ت╠غN╩█╜≡ى~░┘╖╓╓«╬ف╩«╥╘╔╧╢■▒╢╥╘╧┬┴P╜≡ة▒╨▐╕─ئلة░▓ت╠┴P╜≡ة▒ةث╡┌╦─ⁿc╨▐╒²▓ت▓╗═╗╪ث���ثش╘ق╘┌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╓╨╛═╙╨îخ╡┌141ùl╡─ى╦╞╨▐╕─���ثش╟╥îW╜ق╥╤╢ض╙╨╙ّ╒ôثش╥ٌ┤╦�ثش▒╛╬─âHطءîخ╟░╚²é╖╜├µ╡─╨▐╕─╓≡╥╗╖╓╬ِ║═╘uârةث
╥╗���ةت╨╨ئل┐═ٍw╡─╖╓┴ت╥(guذر)╓╞ث║
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╢■╘زà^(qذ▒)╖╓
╝░╞غ║╧└و╨╘
ثذ╥╗ثر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╢■╘ز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╡─┤_┴ت
╝┘╦┼c┴╙╦▓ت┴ت╡─╨╠╩┬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╩╟╓≡▓╜┤_┴ت╡─ةث1979─م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╨╠╖ذة╖╡┌164ùl╥(guذر)╢ذث║ة░╥╘بI└√ئل─┐╡─���ثش╓╞╘ه���ةت╪£┘u╝┘╦╬ث║خ╚╦├ً╜ة┐╡╡─��ثش╠╢■─م╥╘╧┬╙╨╞┌═╜╨╠�����ةت╛╨╥█╗ٌ╒▀╣▄╓╞�ثش┐╔╥╘▓ت╠╗ٌ╒▀╬╠┴P╜≡���ث╗╘ه│╔ç└╓╪║ٍ╣√╡─�ثش╠╢■─م╥╘╔╧╞▀─م╥╘╧┬╙╨╞┌═╜╨╠���ثش┐╔╥╘▓ت╠┴P╜≡��ة����ثة▒╘ôùl┤_┴ت┴╦ة░╓╞╘ه����ةت╪£┘u╝┘╦╫ية▒�����ثش▓تîت╓«╫≈ئلة░╖┴║خ╔قـ■╣▄└و╓╚╨ٌ╫ية▒╓«╥╗╖N╝╙╥╘╢ذ╬╗ثش╡س▓ت╬┤îخة░┴╙╦ة▒╝╙╥╘╨╠╩┬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��ةث
نS║ٍ����ثش1984─مىC▓╝╡─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33ùlةت╡┌34ùl╥(guذر)╢ذ┴╦╜√╓╣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┼c┴╙╦��ثش▓ت╘┌╘ô╖ذ╡─╡┌50ùl��ةت╡┌51ùl╥(guذر)╢ذ┴╦╔·«a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┼c┴╙╦ّز│╨ô·╨╨╒■┼c╨╠╩┬╖ذ┬╔╪ا╚╬ثش┐╔╓^╩╫┤╬┤_┴ت┴╦╝┘╦┼c┴╙╦▓ت┴ت╡─╢■╘ز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���ةث▀@╥╗─ث╩╜╘┌1997─م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╨╠╖ذة╖╓╨▒╗╜╙╩▄���ثش╖╓e╙┌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╥(guذر)╢ذ┴╦ة░╔·«a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ة▒║═ة░╔·«a��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ة▒����ةث╓╡╡├╫ت╥ظ╡─╩╟ثش┼c1979─مة╢╨╠╖ذة╖╧ض▒╚���ثش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ٍw╧╡╬╗╓├╙╨┴╦╨┬╡─╒{╒√�����ثش─ة░╖┴║خ╔قـ■╣▄└و╓╚╨ٌ╫ية▒┼▓╚نة░╞╞ë─╔قـ■╓≈┴x╩╨êِ╜ؤإ·╓╚╨ٌ╫ية▒╓«╓╨�����ةث╙╔┤╦�����ثش▀@╖N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▓ت┴ت╡─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ثش▓╗âH┼c╧ضمP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╛S│╓╓°╛o├▄عـ╜╙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┼c╘ô╒┬╓╨é╬ةت┴╙╔╠╞╖╡─╢■╖╓─ث╩╜▒ث│╓╓°â╚╘┌╞ُ║╧�ةث╓«║ٍثش2011─م═ذ▀^╡─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îخ╔·«a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╙ك╥╘┤ٍ╖∙╨▐╕─ثش╚ق╚ة╧√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╓«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ةت╕─╝┘╦╖╕╫ي╡─▒╢▒╚┴P╜≡╓╞ئلاo╧▐ى~┴P╜≡╓╞╡╚���ثش╡سîخ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╖╓┴ت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às▓ت╬┤╙|╙ةث▒╛┤╬╨╠╖ذ╨▐╒²▀M╥╗▓╜îخ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╙ك╥╘âئ(yذصu)╗»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▀@╖N─ث╩╜╚╘╚╗▒╗╒√ٍw╨╘╡╪╛S│╓╧┬و�ةث┼c╓«╧ضّز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╫╘1984─م╓╞╢ذ╥╘و����ثشنmأv╜ؤ2001─مةت2013─م����ةت2015─م���ةت2019─م╡╚¤╡┤╬╨▐╙ثش╡س▀@╖N╝┘╦┼c┴╙╦▓ت┴ت╡──ث╩╜╥▓╩╝╜K╡├╥╘╛S│╓���ةث
ثذ╢■ثر╝┘╦�ةت┴╙╦╢■╘زà^(qذ▒)╖╓╡─╛▀ٍw╙░وّ
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╢■╘ز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�ثش─╦╥╘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ئل╥(guذر)╖╢▌dٍw║═╕∙ô■����ةث─▀@â╔é╥(guذر)╖╢│ِ░l(fذة)ثش═ذ▀^╫╨╝أ▒╚▌^����ثش╬╥éâ┐╔░l(fذة)شF▀@╥╗─ث╩╜╘┌╥(guذر)╖╢ءï╘ه║═╖ذ┬╔╨د╣√╖╜├µ╡─╛▀ٍw╙░وّةث
╞غ╥╗���ثش╖ذ╥µ╟╓║خ╡─╨╬ّB(tذجi)╙╨e��ةث╔·«a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╡─╖ذ╥µ╟╓║خ╨╬ّB(tذجi)┐╔╓^╥╗▓ذ╚²╒█�����ثش│╩شF│ِ─╜Y╣√╖╕╡╜╛▀ٍw╬ثنU╖╕╘┘╡╜│ل╧ٍ╬ثنU╖╕╡─╫â▀w▄ë█Eةث1979─مة╢╨╠╖ذة╖╩╟╥╘ة░╬ث║خ╚╦├ً╜ة┐╡╡─ة▒ئل▒╛╫ي╓«│╔┴تùl╝■�ثش┐╔╓^╡غ╨═╡─╜Y╣√╖╕ث╗1993─م╚سç°╚╦┤ٍ│ث╬»ـ■ىC╨╨╡─ة╢مP╙┌ّ═╓╬╔·«a��ةتغN╩█é╬┴╙╔╠╞╖╖╕╫ي╡─ؤQ╢ذة╖╡┌2ùlîخ▒╛╫ي╫ِ┴╦╓╪┤ٍ╨▐╕─�����ثش╢ذ╫ي╓╗╨كة░╫ع╥╘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ة▒╝┤┐╔�ثش╙╔┤╦�ثش─╜Y╣√╖╕╕─ئل╛▀ٍw╬ثنU╖╕ث╗▀@╥╗╨▐╕─▒╗1997─مة╢╨╠╖ذة╖╦∙╜╙╩▄��ثش╘┌1997─م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╓╨╡├╥╘├≈┤_│╨╒J���ث╗╞غ║ٍ�����ثش2011─م═ذ▀^╡─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����ثش╙╓h│²┴╦╘صùl╬─╓╨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ة▒╡─▒و╩ِ�ثشâH▒ث┴َ┴╦ة░╔·«a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╡─ة▒▀@╥╗╨╨ئل╥ز╟ٍ��ثش╘ô╫ي╝┤─╛▀ٍw╬ثنU╖╕▐D╫â?yذصu)ل│ل╧ٍ╬ثنU╖╕����ةث╧ض▒╚╢°╤╘ثش╫╘1997─مة╢╨╠╖ذة╖┤_┴ت╥╘و����ثش╔·«a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╡─╖ذ╥µ╟╓║خ╨╬ّB(tذجi)às▒ث│╓╖(wذدn)╢ذ����ثشة░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╘ه│╔ç└╓╪╬ث║خ╡─ة▒╩╝╜K╩╟╞غ▓╗┐╔╖┼ùë╡─╢ذ╫ي╥ز╟ٍةث╙╔┤╦����ثشîخ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╖ذ╥µ╢°╤╘ثش╩╟âH╥ز╟ٍ─│╖N│ل╧ٍ╡─╖ذ╥µ╟╓║خيLنU�ثش▀╩╟▀M╢°╥ز╟ٍ─│╖N╛▀ٍw╡─î║خ╜Y╣√ثشءï│╔┴╦╝┘╦╖╕╫ي┼c┴╙╦╖╕╫ي╘┌╥(guذر)╖╢ءï╘ه╔╧╡─╥╗éي@╓°à^(qذ▒)e��ةث
╞غ╢■�����ثش╥ٌ╣√مP╧╡╝░╞غ╫C├≈╪ôô·╙╨eةثîخ╙┌╔·«a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╢°╤╘�ثشاo╒ô╥ـ╞غئل╨╨ئل╖╕╥╓╗ٌ╩╟│ل╧ٍ╬ثنU╖╕ثش╥ٌ╣√مP╧╡╛∙▓╗│╔ئل╞غî▓لîخ╧ٍ��ةث╧ض╖┤�����ثشîخ╔·«a�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╢°╤╘�ثش╞غ╜Y╣√╖╕╡─ءï╘هt╩╣╥ٌ╣√مP╧╡╡─┼╨¤ض│╔ئل▒╪وأةث╡سûى}╩╟�ثش▀@╖N╥ٌ╣√مP╧╡╡─┼╨¤ض╩╟ءOئل└دنy╡─ث║╩╫╧╚ثش╦╞╖╓┬ôp╡─╨د╣√��ثش║▄┐╔─▄╨ك╥ز▌^لLـrلg▓┼─▄ي@شF�ةت╙^£y║═╘u╣└ثش╨╨ئل┼c╜Y╣√لg┬ô╧╡╡─▀t╛┼c╩ك╦╔�ثش╩╣╥ٌ╣√مP╧╡╡─┼╨¤ض▌^ئل└دنyةث╞غ┤╬��ثش╘┌═نs╡─╥ٌ╣√مP┬ô╓╨��ثش╦╬ي┼c╜ة┐╡ôp║خلg╡─مP╧╡║▄نy▒╗╛س┤_╖╓نxةث▀@╩╟╥ٌئل���ثشôp║خ╜Y╣√╝╚┐╔─▄┼c╙╨╚▒╧▌╡─╦╬ي╧ضمP��ثش╥▓┐╔─▄╩╟╝▓▓ة▒╛╔و╡─░l(fذة)╒╣┼c║╗»╦∙╓┬���ثش╥ض┐╔─▄┼c╖■╦╒▀╫╘╔و╡─ٍw┘|╧ض▀Bثش▀┐╔─▄╩╟╢ض╖N╥ٌ╦╪╡─╗ح╙╜Y╣√���ةث╥زîت╦╬يîخôp║خ╜Y╣√╡─╫≈╙├مP╧╡╝░╫≈╙├┴خ┤ٍ╨ة£╩┤_╡╪─╓╨═╕╬ِ│ِو�����ثشاo╥╔╖╟│ث└دنy�����ةث╫ى║ٍ���ثشكb╢ذ╚▒╧▌╦╞╖╡─╓┬ôpآC└وثش╥└┘ç╙┌╠╪e╡─îثءI(yذذ)╓ز╫R┼c╝╝╨g╩╓╢╬����ثش▀@═شء╙┐╔─▄│╔ئلî█`╓╨╡─╒╧╡K�ةث╒²╩╟╗∙╙┌╔╧╩ِ└دنy�����ثش╔·«a��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╡─îنH╫╖╘V╫â╡├ءOئل╞Dنy�����ثش╔ُ╓┴╩╣╘ôùl┐ى│╔ئل╜ر╩شùl┐ى���ةث╚ق╣√╥╘╔·«aةتغN╩█┴╙╦ئلمPµI╘~╘┌╓╨ç°▓├┼╨╬─ـ°╛W╔╧▀M╨╨╦╤╦≈�����ثش┐╔╥╘░l(fذة)شF�ثش2010─م╥╘و╙╨64é╧ضمP╨╠╩┬░╕╝■ةث╘┘╓≡╥╗┼┼▓ل�ثش╞غ╓╨╓╗╙╨1╝■╥╘╔·«a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╢ذ╫ي��ثش┤ٍ▓┐╖╓╛∙╥╘╔·«aةتغN╩█é╬┴╙«a╞╖╫ي╝╙╥╘╠┴P�ةث
╞غ╚²ثش╖ذ╢ذ╨╠╘O╓├╙╨e��ة�ث┐╔╥╘┐┤╡╜ثش╘┌╖ذ╢ذ╨╠╘O╓├╔╧�����ثش╔·«a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║═╔·«a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╥▓┤µ╘┌╧ض«¤à^(qذ▒)e���ةث╓≈╥زٍwشF╘┌ث║╟░╒▀╡─╖ذ╢ذ╫ى╕▀╨╠╕ⁿ╓╪��ثشئل╦└╨╠����ثش╢°║ٍ╒▀ئلاo╞┌═╜╨╠���ث╗╟░╒▀╡─╞≡╨╠ⁿc╕ⁿ╡═����ثشئلة░╚²─م╥╘╧┬╙╨╞┌═╜╨╠╗ٌ╒▀╛╨╥█ثش▓ت╠┴P╜≡ة▒�ثش╢°║ٍ╒▀╡─╞≡╨╠ⁿctئلة░╚²─م╥╘╔╧╩«─م╥╘╧┬╙╨╞┌═╜╨╠ثش▓ت╠┴P╜≡ة▒��ث╗╟░╒▀╡─╨╠آn╘O╓├╕ⁿئل╝أ├▄��ثش╖ذ╢ذ╨╠▒╗╖╓ئل╚²آn����ثش╢°║ٍ╒▀t╖╓ئلâ╔آnث╗╨╠آnإ╖╓╡─ء╦£╩▓╗═ش���ثش╟░╒▀│²┴╦ة░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╘ه│╔ç└╓╪╬ث║خة▒ة░╓┬╚╦╦└═ِة▒╡╚║ٍ╣√╨═ء╦£╩╓«═ظثش▀╥²╚ن┴╦ة░╞غ╦√ç└╓╪╟ل╣إ(jiذخ)ة▒ة░╞غ╦√╠╪eç└╓╪╟ل╣إ(jiذخ)ة▒╡╚╕ⁿئل╛C║╧╡─╟ل╣إ(jiذخ)╨═ء╦£╩�����ثش║ٍ╒▀t╥╘ة░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╘ه│╔ç└╓╪╬ث║خ╡─ة▒ة░║ٍ╣√╠╪eç└╓╪╡─ة▒ئل╘O╓├╗∙£╩�����ثش┼┼│²┴╦║ٍ╣√╓«═ظ╕ⁿئلل_لا╡─╟ل╣إ(jiذخ)╨╘┐╝┴┐ثش├≈ي@▓╔╚ة┴╦╬ذ║ٍ╣√╒ô╡─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���ةث
ثذ╚²ثر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à^(qذ▒)╖╓╗∙£╩╡─و╘┤
╙╔╙┌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┼c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╘┌▒ث╫o┐═ٍw��ةت╨╨ئل╖╜╩╜�ةت╨╨ئل╓≈ٍwةت╫ي▀^╨─└و╡╚╖╜├µ▓ت▓╗┤µ╘┌├≈ي@à^(qذ▒)e�ثش╨╨ئل┐═ٍw╡─à^(qذ▒)╖╓▒عي@╡├╙╚ئل╓╪╥زةث╨╨ئل┐═ٍw╡╜╡╫╩╟╝┘╦▀╩╟┴╙╦���ثشـ■╘┌╥(guذر)╖╢ءï╘ه┼c╖ذ┬╔╨د╣√╔╧«a╔·▌ù╔غ╨╘╡─╓╪┤ٍ╙░وّ��ةث╔╧├µ╦∙╙ّ╒ô╡─╚²é╖╜├µ╝┤╩╟╞غ╛▀ٍwي@شF�����ة�ث┐╔╥╘╒fثش▀@╖N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╢■╘ز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����ثش╓«╦∙╥╘╡├╥╘▀\╨╨ثش╓«╦∙╥╘╡├╥╘║╧└و╗»�����ثش╩╟╥ٌئل╜y╜yب┐╧╡╙┌╝┘╦┼c┴╙╦à^(qذ▒)╖╓╗∙£╩╡─╒²«¤╨╘�ةث
1997─م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├≈┤_╥(guذر)╢ذثشة░▒╛ùl╦∙╖Q╝┘╦����ثش╩╟╓╕╥└╒╒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╥(guذر)╢ذî┘╙┌╝┘╦║═░┤╝┘╦╠└و╡─╦╞╖ةت╖╟╦╞╖ة▒��ثش╡┌142ùl╥▓╙╨ى╦╞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��ةث2011─م╡─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▒M╣▄îخ╦╞╖╖╕╫ي╝╙╥╘╓╪┤ٍ╨▐╙�ثش╡س╚╘╛S│╓┴╦┤╦╖N╫ً╤ص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╡─╜ق╢ذ╦╝┬╖ةث╚╗╢°▒╛┤╬╡─╨╠╖ذ╨▐╙����ثشàsءOئل┤ٍ─ّ╡╪h│²┴╦╔╧╩ِ╥(guذر)╢ذةث▀@╩╟╖ً╛═╥ظ╬╢╓°��ثش╘┌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╒J╢ذ╗∙£╩╔╧�ثش╨╠╖ذîت┼c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╖╓╡└ôPكsث┐
ّز«¤│╨╒J����ثش▀@╥╗h│²îنH╔╧╘┤╙┌مّ╙┬░╕╦∙«a╔·╡─╛▐┤ٍ╔قـ■ë║┴خثش╝░┴ت╖ذ╒▀îخمّ╙┬░╕╡─╔ى┐╠╖┤╦╝�����ةثمّ╙┬╘┌ؤ]╙╨╚ة╡├▀M┐┌┼·╬─╡─╟لؤr╧┬����ثش─╙ة╢╚┘▀M╚≡╩┐ة░╕ً┴╨╨l(wذذi)ة▒╡─╖┬╓╞╦ثش▓ت╥╘├┐║╨200╢ض╘ز╡─âr╕ً┘u╜o╞غ╦√▓ة╙╤���ةث▀@╖N╖┬╓╞╦╖■╙├╓«║ٍ����ثش╛▀╙╨┼cة░╕ً┴╨╨l(wذذi)ة▒┤ٍ╓┬╧ض«¤╡─»ا╨دةث╕∙ô■«¤ـr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╝┘╦وأ╥└╒╒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╧ضمP╥(guذر)╢ذ╝╙╥╘╒J╢ذ��ةث╢°«¤ـr╡─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╓╨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ة░▒╪وأ┼·£╩╢°╬┤╜ؤ┼·£╩╔·«a����ةت▀M┐┌ثش╗ٌ╒▀▒╪وأآzٌئ╢°╬┤╜ؤآzٌئ╝┤غN╩█╡─ة▒��ثش░┤╒╒╝┘╦╒ô╠�ةث╘┌╛▐┤ٍ╡─╔قـ■▌ؤ╒ôë║┴خ╧┬ثش▒M╣▄مّ╙┬░╕╥╘ة░▓╗ءï│╔غN╩█ة▒╡─╙╪╗╪└و╙╔╢°▓╗╞≡╘V���ثش╡س╞غ╦∙┤·┘╓«╦╞╖àsنy╠╙ة░╝┘╦ة▒╓«╒J╢ذ���ةث╙╔╙┌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îت╬╝â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═ذ▀^¤M╓╞╡─╖╜╩╜╙▓╚√╚نة░░┤╝┘╦╒ôة▒╓«╓╨ثش▓╗╡س╩╣╝┘╦╕┼─ى╡─╝â┤ظ╨╘╙╨╦∙ôpé√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╩╣╞غ║╧└و╨╘╥▓éغ╩▄┘|╥╔ةث╫ىئل═╗│ِ╡─▒وشF╩╟ثش▒M╣▄╬┤╜ؤ┼·£╩▀`╖┤┴╦╨╨╒■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▀M┐┌╡─╦╞╖àsاoôp╔ُ╓┴╙╨└√╙┌╚╦ٍw╜ة┐╡��ثش╩╟╖ًّز«¤ءï│╔╝┘╦��ث┐╒²╩╟╗∙╙┌îخمّ╙┬░╕╡─╖┤╦╝���ثش2019─م12╘┬1╚╒╞≡î╩ر╡─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ثشîخ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▀M╨╨┴╦╓╪╨┬╒{╒√�ثش╠╪e╩╟îت╘ص╧╚╡─¤M╓╞╨═╝┘╦ةت¤M╓╞╨═┴╙╦╙ك╥╘┤ٍ╖∙╢╚╡╪âنx�ةث╘┌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╥╤╜ؤîخ╝┘╦ةت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╝╙╥╘âئ(yذصu)╗»╡─▒│╛░╧┬��ثش╚ق╣√ة╢╨╠╖ذة╖h│²╡┌141ùl��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╡─╡┌2┐ى����ثش╛═╥ظ╬╢╓°╪╡╫ْùë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╒J╢ذ╗∙£╩ثش╞غîنHâr╓╡┐╔─▄ـ■┤ٍ┤ٌ╒█┐█�ةث
╧ض╖┤��ثش╚ق╣√╘┌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╒J╢ذء╦£╩╔╧╫ً╤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ثش┐╔─▄îت«a╔·╓T╢ضî╥µ����ةث╩╫╧╚ثش╙╨╓·╙┌╒J╢ذء╦£╩╡─╜y╥╗╨╘�����ة���ث╗∙╙┌╖ذ╓╚╨ٌ╡─╜y╥╗╘ص└و�����ثش╫≈ئل▒ث╒╧╖ذ╡─╨╠╖ذ╚ق┼c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╒J╢ذء╦£╩▒ث│╓╥╗╓┬�����ثشîت╫ى┤ٍ╧▐╢╚╡╪╘ِ▀M╖ذ╕┼─ى┼c╖ذٍw╧╡╡─â╚▓┐╚┌╪ئ╨╘����ثش╥▓îت╫ى┤ٍ╧▐╢╚╡╪£p╔┘╦╛╖ذ╓╨┐╔─▄╡─ود╥ظ┼c▓ىeîخ┤²ةث╞غ┤╬�����ثش╙╨╓·╙┌┼╨¤ض╔╧╡─╜ؤإ·╨╘┼c╨د┬╩╨╘�ةث╫ً╤ص╨╨╒■╖ذ╔╧╡─╒J╢ذء╦£╩╢°▓╗╩╟┴و╞≡بt╘ى�����ثش╩╣╨╨╒■╖ذ╔╧╡─┼╨¤ض│╔ئلàت┐╝╗∙£╩╢°اoوأ╖┤═┼╨¤ض���ثشîتي@╓°╠ط╔²┼╨¤ض╡─╨د┬╩���ثش┤┘▀M╦╝┐╝╡─╜ؤإ·╨╘ةث╘┘┤╬���ثش╙╨╓·╙┌╒J╢ذء╦£╩╡─îثءI(yذذ)╨╘���ةث╦╞╖╩╟╖ً┤µ╘┌╚▒╧▌ثش──╨ر╚▒╧▌îتîخ╦╞╖╡─╣خ╨د«a╔·╙░وّثش╙░وّ╡─│╠╢╚┼c╖╢ç·╚ق║╬����ثش▀@╨رûى}╢╝╨ك╥زîثلT╓ز╫Rةت╜ؤٌئ┼c╝╝╨g╖╜─▄╗╪┤≡��ةث╢°╫≈ئل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╞≡▓▌╒▀╡─╨╨╒■آCمP��ثشي@╚╗╘┌îثءI(yذذ)ىI╙ٌâ╚╕ⁿ╛▀╙╨╓ز╫R┼c╝╝╨g╔╧╡─âئ(yذصu)╘╜╨╘��ةث═┤╬�ثشîشF╫Cô■╡─┐╔▐DôQ╨╘ةث╫╖╘VآCمPîخ╙┌╫Cô■╡─╩╒╝»║═╒√└و��ثش╘┌╧ض«¤│╠╢╚╔╧╥└┘ç╙┌╨╨╒■آCمP╡─╓د│╓�����ثش╠╪e╩╟╦╞╖▒O(jiذةn)╢╜╣▄└و▓┐لT╡─╓د│╓��ةث╚ق╣√╘┌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╒J╢ذء╦£╩╔╧▒ث│╓╥╗╓┬�����ثشîت╫ى┤ٍ╧▐╢╚╡╪▒ع└√╙┌╫Cô■╡─╣╠╢ذ�����ةت╥╞╜╗║═▐DôQةث═شـr��ثش╘┌î┼╨▀^│╠╓╨���ثش«¤╦╞╖╩╟╖ًî┘╙┌╝┘╦╗ٌ┴╙╦┤µ╘┌╥╔┴xـr����ثش═ذ│ث╨ك╥ز╜ك╓·╦╞╖▒O(jiذةn)╣▄▓┐لT╡─كb╢ذ╝╙╥╘│╬╟ف�����ةث║┴اo╥╔û��ثش┤╦╖Nكb╢ذ═ذ│ث╥▓╩╟╕∙ô■╨╨╒■╖ذ╔╧╡─╧ضمPء╦£╩و▀M╨╨╡─����ةث╫ى║ٍ��ثش╘ِ▀M╒J╢ذء╦£╩╡─ه`╗ى╨╘┼c╗╪ّز╨╘�����ةث╧ض▒╚╨╠╖ذ╢°╤╘ثش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╘┌╨▐╕─│╠╨ٌ╔╧╕ⁿئلîْ╦╔�ثش╥▓╕ⁿ╥╫╘┌┴ت╖ذ╡─╗ى╨╘╗»╖╜├µ┌A╡├╧╚آCةث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╒J╢ذء╦£╩���ثشّز┼cطt(yذر)╦╨╨ءI(yذذ)╡─░l(fذة)╒╣╫â╙╣إ(jiذخ)┼─╥╗╓┬��ثش╨ك▒ث│╓▀m«¤╡─ه`╗ى╨╘�����ةث╛═┤╦╢°╤╘����ثش╥╘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╡─╨╬╩╜┤_┴ت╞غ╒J╢ذء╦£╩�ثش╥▓╕ⁿ╛▀▀mـr╗╪ّز╡─╓╞╢╚âئ(yذصu)▌ةث
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îت╘ص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╡┌2┐ى╙ك╥╘╓▒╜╙h│²��ثش║▄╚▌╥╫▒╗└و╜ظئل╝┘┴╙╦╒J╢ذء╦£╩┼c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╪╡╫├ôع^��ةث╡س╗∙╙┌╔╧╩ِ╖╓╬ِ��ثش▒╛╬─╥╘ئل�ثش▀@╖N└و╜ظ╖╜╩╜نm╛▀╙╨▒و├µ║╧└و╨╘ثش╡س╘┌îنH╨د╥µ╔╧às╙╨╛▐┤ٍôpé√�ةث╥ٌ┤╦ثش▓╗╖┴îت▀@╖Nh│²└و╜ظئل╥╗╖Nة░╥(guذر)╖╢╛╨╩°╡─╦╔╜ëة▒�����ثش╥╗╖Nة░├≈├µ╔╧╡─├ôع^ة▒����ةث╛▀ٍw╢°╤╘ث║╞غ╥╗ثش─▀ë▌ï╔╧┐┤�����ثش▓╗─▄îت▀@╥╗h│²└و╜ظئلة░╜^îخ▓╗─▄╥└╒╒ة▒����ةث╘ص╡┌2┐ى╡─╥ظ║ص╘┌╙┌����ثش╨╠╖ذ╔╧╝┘┴╙╦╡─╒J╢ذ▒╪وأ╥└╒╒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╧ضمP╥(guذر)╢ذةث╥ٌ┤╦�����ثش▀@╥╗h│²╓╗╩╟îخة░▒╪وأ╥└╒╒ة▒├ⁿ┴ى╡─╚ح│²ثش╢°▓ت▓╗╥ظ╬╢╓°ة░▓╗£╩╥└╒╒ة▒╡─╜√┴ى┤_┴ت�ةث╞غ╢■ثش─╜ؤٌئ╜╟╢╚╙^▓ه��ثش╨╠╖ذ╘┌î█`▓┘╫≈╓╨╚╘ـ■╫ً─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╔╧╡─╧ضمP╜ق╢ذ���ثش▓ت╫ى┤ٍ╧▐╢╚╡╪▒ث│╓┼╨¤ض╡─╜y╥╗╨╘�����ةت╜ؤإ·╨╘�ةتîثءI(yذذ)╨╘┼c╗╪ّز╨╘�����ةث╡س╩╟��ثش▀@╖N╫ً─╩╟╥╗╖N╩┬î╨╘╡─╫ً─����ثش╢°╖╟╥(guذر)╖╢╨╘╡─╫ً─ةث╘ص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╡┌2┐ى╡─h│²�ثش╥ظ╬╢╓°╥╗╖Né╨╘╡─ةت╥(guذر)╖╢╨╘╡─╝s╩°╡─╚ح│²�ةث╞غ╚²ثش─│╠╢╚╔╧╙^▓ه�����ثش╨╠╖ذîخ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╧ضمP╜ق╢ذ╡─╫ً─��ثش╩╟╥╗╖N╧ضîخ╡─╫ً╤ص╢°╖╟╜^îخ╡─╫ً╤ص�����ة�����ث╗∙╙┌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┼c╔قـ■╚╬╒╡─à^(qذ▒)e����ثش╨╠╖ذ╡─╥(guذر)╖╢└و╜ظ╚╘╚╗╛▀╙╨╞سنx╙┌╟░╓├╖ذ▓ت▀M╨╨زأ┴ت┼╨¤ض╡─┐╔─▄�ةث╢°▀@╥╗╧ضîخ╗»┼╨¤ض╡─┐╒لgثش╒²╩╟╙╔▒╛┤╬╨▐╒²╦∙ô(chuذجng)╘ه��ةث
ثذ╦─ثر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à^(qذ▒)╖╓╗∙£╩╡─═╫«¤╨╘
╙╔╔╧╦∙╓ز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╨مP╙┌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ء╦£╩�ثش╚╘ـ■╘┌╧ض«¤│╠╢╚╔╧│╔ئل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╡─╒J╢ذàت╒╒�����ةث╥ٌ┤╦��ثش╒J╒µî╥ـ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╨╡─╧ضمP╜ق╖╓ء╦£╩����ثش╥└╚╗╛▀╙╨╨╠╖ذ▀m╙├╒ô╔╧╡─╓╪╥زâr╓╡ةث
1.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╨▐╒²
╘┌2019─م12╘┬1╚╒ل_╩╝╩ر╨╨╡─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�ثشîخ╘ص╡┌48ùlثذ╝┘╦┼c░┤╝┘╦╒ôثرةت╡┌49ùlثذ┴╙╦┼c░┤┴╙╦╒ôثر╡─╥(guذر)╢ذ▀M╨╨┴╦╨▐╒²�ةت╒{╒√┼c╓╪╨┬╒√║╧ةث
╩╫╧╚�����ثش╚ة╧√┴╦╘صو¤M╓╞╨═╝┘╦┼c¤M╓╞╨═┴╙╦╡─╧ضمP╥(guذر)╢ذ��ةثîت╞غ╓╨▓┐╖╓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╨ئل│ل╚ة│ِو▓ت▀m«¤╤a│غ║ٍ���ثشزأ┴ت╡╪╓├╚ن╡┌124ùl╓╨╝╙╥╘╥(guذر)╓╞�ةث╚ق┤╦╥╗وثش╘┌╝┘╦┼c┴╙╦╓«لg▒M╣▄┤µ╘┌à^(qذ▒)e��ثش╡سâ╔╒▀┼c╬╝â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├≈ي@└صل_╛ضنx�����ثش╨╬│╔┴╦╥╗é╥╘╦╞╖ء╦£╩ئل║ظ┴┐ء╦│▀╡─╖╢«بٍw╧╡�ةث
╞غ┤╬ثش╝┘╦╡─╕┼─ى╕ⁿئل╝â╗»���ةث╘┌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╡┌48ùl╓╨�����ثش╝┘╦╡─╜ق╢ذ▓╔╚ة┴╦ة░2+6ة▒─ث╩╜��ثش╟░2╖Nئل╝┘╦╡─╥╗░ع╟ل╨╬��ثش║ٍ6╖Nئل░┤╝┘╦╒ô╡─╟ل╨╬����ةث╢°╘┌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���ثشâ╔╖N╝┘╦╡─╥╗░ع╟ل╨╬╡├╥╘▒ث┴َ����ثش╡س╦─╖N░┤╝┘╦╒ô╡─╟ل╨╬╓╨��ثشtâH╙╨╡┌ثذ3ثر╖N�ةت╡┌ثذ6ثر╖N╟ل╨╬╡├╥╘▒ث┴َةث╚ق┤╦╥╗و��ثش╝╚╙╨╡─╝┘╦╕┼─ى╕ⁿ╚▌╥╫╩╒¤┐╘┌─│╖Nî┘|╡─�����ةت╣خ─▄╨╘╡─╥ـ╜╟╓«╧┬�����ثش─╩╟╖ً╛▀éغ╧ضّز╡─╦╬ي│╔╖▌┼cîنH»ا╨دء╦£╩و╜y╥╗░╤╬╒���ةث╘┌▀@╥╗ء╦£╩╧┬���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╡─╡┌ثذ1ثر╖N╟ل╨╬ثش╩╟╦╬ي│╔╖▌▓╗╖√îد╓┬╦╨د▓╗▀_�����ث╗╘┌╡┌ثذ2ثر╖N╟ل╨╬╧┬ثش╥╘╖╟╦╞╖├░│غ╦╞╖╗ٌ╥╘╦√╖N╦╞╖├░│غ┤╦╖N╦╞╖���ثش╥ض╩╟╥ٌئل╚▒╔┘╠╪╢ذ╦╬ي╡─╙╨╨د│╔╖▌╢°îد╓┬╦╨د╩▄ôp╗ٌ╒√ٍw╟╖╚▒�ث╗╘┌╡┌ثذ3ثر╖N╟ل╨╬╧┬���ثش╦╞╖╫â┘|┐╔─▄îد╓┬│╔╖▌╫â╗»����ثش─╢°╙░وّ╦╬ي»ا╨د╡─░l(fذة)ô]�ث╗╢°╘┌╡┌ثذ4ثر╖N╟ل╨╬╓╨ثشء╦├≈╡─▀mّز░Y╗ٌ╣خ─▄╓≈╓╬│ش│ِ╖╢ç·��ثش▒و├µ╔╧┐┤╩╟ء╦╫R╗ٌ╨╬╩╜ûى}����ثش╡سîنH╔╧╩╟îت╨╬╩╜╗»ء╦╫R┼c│╔╖▌ءï│╔╧ض▒╚îخ╡─╥ظ┴x╔╧╡├│ِ╡─╒J╢ذ╜Y╒ôثش▀╩╟┐╔╥╘╗╪╡╜╦╬ي│╔╖▌▓╗╖√┼c╣خ─▄ôpé√╓«╔╧���ةث
╫ى║ٍ�ثش┴╙╦╕┼─ى╡─╛╓▓┐âئ(yذصu)╗»���ةث╘┌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9ùl╓╨�����ثش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▓╔╚ة┴╦ة░1+6ة▒─ث╩╜���ثش╝┤╧╚îخ┴╙╦╜o│ِ╥╗░ع╨╘╡─╜ق╢ذثش╚╗║ٍîخ6╖N░┤┴╙╦╒ô╡─╟ل╨╬╙ك╥╘┴╨┼e╩╜╥(guذر)╢ذ�ةث╢°╡╜┴╦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╡┌98ùl╓╨ثش╘صو╡┌49ùl╓╨░┤┴╙╦╒ô╡─ثذ1ثرثذ2ثرثذ3ثرثذ6ثر╦─╖N╟ل╨╬╡├╥╘╓▒╜╙▒ث┴َ����ثش▓ت─░┤┴╙╦╒ô╫â?yذصu)ل┴╙╦ث╗╘ص╡?9ùl╓╨░┤┴╙╦╒ô╡─╡┌ثذ5ثر╖N╟ل╨╬▒╗╨▐╕─��ثشh│²┴╦╞غ╓╨╔├╫╘╠و╝╙╓°╔سر�����ةت╧ع┴╧��ةت│C╬╢ر╡─╦╞╖�����ثش▒ث┴َ┴╦╔├╫╘╠و╝╙╖└╕»ر║═▌o┴╧╡─╦╞╖ثش│╔ئلشF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┴╙╦╡─╡┌ثذ6ثر╖N╟ل╨╬�����ث╗╢°╘ص╡┌49ùl╓╨░┤┴╙╦╒ô╡─╡┌ثذ4ثر╖N╟ل╨╬�����ثش╝┤ة░╓▒╜╙╜╙╙|╦╞╖╡─░ⁿ╤b▓─┴╧║═╚▌╞≈╬┤╜ؤ┼·£╩╡─ة▒�ثش╝╚╬┤▒╗╝{╚ن┴╙╦║═╝┘╦╡─╖╢«ب╓«╓╨ثش╥▓╬┤╘┌شF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╓╨╙ك╥╘╥(guذر)╓╞�ثش╢°╩╟╘┌شF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╥╘╬┴╨╜√╓╣╡─╨╬╩╜ثش╕╜╓°╘┌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╥(guذر)╢ذ╓«║ٍ�ةث═شـrثش╘┌╡┌125ùl╓╨╥(guذر)╢ذ┴╦╔·«a��ةتغN╩█┤╦ى╦╞╖╡─╨╨╒■╪ا╚╬���ةث
▓╗نy░l(fذة)شF��ثش▀@┤╬╨▐╒²îخ┴╙╦╡─╨▐╕─╖∙╢╚▌^╨ة��ثش╓≈╥ز╝»╓╨╘┌╚²ⁿcث║╥╗╩╟��ثشîت╔├╫╘╠و╝╙╓°╔سر��ةت╧ع┴╧�����ةت│C╬╢ر╡─╦╞╖����ثش┼┼│²╘┌┴╙╦╓«═ظ�����ةث▀@╩╟╥ٌئل��ثش╕∙ô■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9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��ثشة░╔├╫╘╠و╝╙╓°╔سر��ةت╖└╕»ر�ةت╧ع┴╧ةت│C╬╢ر╝░▌o┴╧╡─ة▒�����ثش░┤┴╙╦╒ô╠ةث▀@ي@╚╗╩╟îت╔╧╩ِ╬ف╖N╟ل╨╬╫≈▓ت┴╨└و╜ظ����ةث╚╗╢°ثش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╕╜t╡┌101ùl╙╓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�ثشة░▌o┴╧ثش╩╟╓╕╔·«a╦╞╖║═╒{┼غ╠╖╜ـr╦∙╙├╡─╕╜╨╬ر║═╕╜╝╙رة▒�����ةث╥╗░عو╒f��ثش╓°╔سر�����ةت│C╬╢ر����ةت╧ع┴╧╡╚╛∙î┘╙┌╕╜╝╙ر╡─╖╢«بثش╘┌▀ë▌ï╔╧ّز╘ô▒╗░ⁿ║ش╘┌▌o┴╧╓«╓╨��ثش╢°╖╟▓ت┴╨مP╧╡�ةث╥ٌ┤╦��ثش┤╦┤╬╨▐╙┐╔╓^╕ⁿ╒²┴╦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9ùl╡─▀ë▌ïفe╒`���ةث╢■╩╟ثشîتة░╓▒╜╙╜╙╙|╦╞╖╡─░ⁿ╤b▓─┴╧║═╚▌╞≈╬┤╜ؤ┼·£╩╡─ة▒╙ك╥╘╬┴╨�ثش▓ت┼┼│²╘┌┴╙╦╖╢«ب╓«═ظةث▀@╩╟╥ٌئل�ثش╓▒╜╙╜╙╙|╦╞╖╡─░ⁿ╤b▓─┴╧┼c╚▌╞≈ثش▒M╣▄╘┌╞غ░▓╚س╨╘╖╜├µ╙╨ç└╕ً╥ز╟ٍ��ثش╡س▓ت╖╟╥╗╜ؤ╩╣╙├����ثش▒ع╥╗╢ذـ■îد╓┬╦╞╖▒╗╬█╚╛╗ٌ│╔╖▌║ش┴┐░l(fذة)╔·╫â╗»����ةث╝┤╩╣░l(fذة)╔·▀@ء╙╡─╫â╗»ثش╥▓┐╔╥╘▒╗░ⁿ└ذ╡╪╘uâr╘┌╡┌98ùl┴╙╦╢ذ┴x╡─╡┌ثذ1ثر ثذ2ثروù╓«╓╨���ثش╥ٌ╢°اoوأ╬زأ╥(guذر)╢ذ�ةث╚²╩╟�����ثشîتة░▒╗╬█╚╛╡─╦╞╖ة▒ثش─╘صو╡┌48ùl╓╨╡─░┤╝┘╦╒ô���ثش▐DئلشF╨╨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╡─┴╙╦���ةث▀@╥╗╒{╒√╡─╘ص╥ٌ┐╔─▄╘┌╙┌ثش╦╞╖▒╗╬█╚╛╓«╟░▓ت╖╟╝┘╦��ثش▒╗╬█╚╛╓«║ٍ▒M╣▄│╔╖▌╗ٌ║ش┴┐┐╔─▄░l(fذة)╔·╫â╗»����ثش╡سنy╥╘╥╗╕┼╒J╢ذئل╝┘╦ةث▀@╥╗╨▐╙┐╔─▄╥²░l(fذة)╝┘╦┼c┴╙╦╓«لg╡─▀à╜ق║ش╗ه��ثشنy╤╘│╔╣خ�ثش║ٍ╙╨╘¤╩ِةث
2.╝╚╙╨à^(qذ▒)╖╓ء╦£╩╡─ûى}╦∙╘┌
ثذ1ثر╕┼─ى╔╧╡─╕é║╧
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▒M╣▄îخ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▀M╨╨┴╦┤ٍ╡╢لا╕س╡─╨▐╙��ثش╡س╚╘┤µ╘┌▓╗╔┘╚▒║╢�ةث╫╨╝أî╥ـشF╨╨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ثشـ■░l(fذة)شFâ╔╒▀┤µ╘┌╕┼─ى╔╧╡─╕é║╧مP╧╡�����ةث
─╡┌98ùlمP╙┌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و┐┤ثش▓╔╚ة┴╦┴╨┼e╝╙╢╡╡╫╡─┴ت╖ذ╖╜╩╜��ثش╟░6╖N╟ل╨╬ئل┴╨┼e╩╜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╡┌7╖N╟ل╨╬tئل╢╡╡╫╩╜╥(guذر)╢ذ�ةث╚ق┤╦╥╗وثشة░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�ثش┐╔▒╗╥ـئل╩╟┴╙╦╡─╥╗░ع╢ذ┴xةث┼c▀@╖N╧ضîخل_╖┼╡─├ك╩ِ╖╜╩╜╧ضîخ�ثش╝┘╦t▓╔╚ة╕F▒M┴╨┼e╡─ةت╧ضîخ╖ظل]╡─╜ق╢ذ╖╜╩╜����ةث▓╗▀^ثش╚ق╣√─┴╙╦╡─╥╗░ع╢ذ┴x│ِ░l(fذة)�ثش╡┌98ùl╦∙┴╨┼e╡─4╖N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ثش╫║ُ╢╝╘┌─│╖N╥ظ┴x╔╧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ء╦£╩���ثش╝┤╢╝╠╙┌┴╙╦╥╗░ع╢ذ┴x╡─║ص¤z╖╢ç·╓«â╚��ةث
╛▀ٍw╢°╤╘��ثش╡┌ثذ1ثر╖N╟ل╨╬╓▒╜╙▒و├≈┴╦ة░╦╞╖╦∙║ش│╔╖▌┼c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╥(guذر)╢ذ╡─│╔╖▌▓╗╖√ة▒�����ث╗╡┌ثذ2ثر╖N╟ل╨╬ة░╥╘╖╟╦╞╖├░│غ╦╞╖╡─╟ل╨╬ة▒�ثش▒╪╚╗▓╗╖√║╧╠╪╢ذ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ث╗╡┌ثذ3ثر╖N╟ل╨╬ة░╫â┘|╡─╦╞╖ة▒�ثش═شء╙▓╗╖√║╧╠╪╢ذ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ث╗╡┌ثذ4ثر╖N╟ل╨╬ة░╦∙ء╦├≈╡─▀mّز░Y╗ٌ╣خ─▄╓≈╓╬│ش│ِ╥(guذر)╢ذ╖╢ç·╡─╦╞╖ة▒�����ثشt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╡─ء╦╫R╥ز╟ٍ╗ٌ╨╬╩╜ء╦£╩�ةث
┐╔─▄┤µ╘┌ب╫h╡─╩╟╡┌ثذ2ثر╖N╟ل╨╬╓╨╡─ة░╥╘╦√╖N╦╞╖├░│غ┤╦╖N╦╞╖ة▒ة��ثة░╦√╖Nة▒┼cة░┤╦╖Nة▒ّز╚ق║╬└و╜ظ�ث┐╩╟└و╜ظئل╦╬ي╖Nىطث┐▀╩╟░ⁿ└ذ╞╖┼╞╡╚╞غ╦√┐╔─▄║ش┴x��ث┐╟░╥╗╖N└و╜ظ╚ق���ثش╙├╕╨├░╦├░│غ░l(fذة)ا²╦����ث╗║ٍ╥╗╖N└و╜ظ╚قثش╙├╞╒═ذ╕╨├░╦و├░│غ─│├√┼╞╕╨├░╦�����ةث╚ق░┤╡┌╥╗╖N└و╜ظ�ثش└و╜ظئل╦╞╖ى╨═╡─├░│غثش─╟├┤���ثش├░│غ╡─╦╞╖╛═▒╪╚╗▓╗╖√║╧╠╪╢ذى╨═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�����ث╗╚ق░┤╡┌╢■╖N└و╜ظ���ثشt╦╞╖│╔╖▌┐╔─▄═م╚س╥╗╓┬ثش╡س╩╟��ثش╘┌╦╞╖░ⁿ╤b┼cء╦╫R╔╧╥▓ـ■▀`▒│╧ضمP╡─╨╬╩╜ء╦£╩��ةث╥ٌ┤╦����ثشاo╒ô╚ق║╬��ثشة░╥╘╦√╖N╦╞╖├░│غ┤╦╖N╦╞╖ة▒╢╝┐╔─▄▀`╖┤╦╞╖╡─î┘|╗ٌ╨╬╩╜ء╦£╩ةث
ثذ2ثر╛▀ٍwى╨═╡─╗ه═ش
╝┘╦┼c┴╙╦▓╗âH┤µ╘┌╕┼─ى╔╧╡─╕é║╧�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╘┌╛▀ٍwى╨═╔╧╜ق╧▐─ث║²��ةث└²╚ق�����ثش╕∙ô■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��ثشة░╦╞╖╦∙║ش│╔╖▌┼c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╥(guذر)╢ذ╡─│╔╖▌▓╗╖√ة▒ئل╝┘╦��ثشة░╦╞╖│╔╖▌╡─║ش┴┐▓╗╖√║╧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ة▒ئل┴╙╦���ةث▀@╥ظ╬╢╓°�����ثش│╔╖▌▓╗╖√╩╟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ثش╢°│╔╖▌╧ض╖√╡س║ش┴┐▓╗╖√t╩╟┴╙╦�ةث╡سûى}╩╟ثش│╔╖▌▓╗╖√┼c║ش┴┐▓╗╖√▓ت╖╟ôً╥╗مP╧╡���ثش╚ق╣√─│╖N╦╞╖╡─▓┐╖╓│╔╖▌▓╗╖√║╧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�ثش═شـr�ثش╞غ╙ض│╔╖▌╡─║ش┴┐╥▓▓╗╖√║╧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ـrثشّز╚ق║╬╒J╢ذ��ث┐▀M╥╗▓╜╡╪�����ثش║ش┴┐▓╗╖√╩╟╥╗éءOئلîْV╡─╖╢«ب�����ثش─╛▀éغ╧ضّز╦╞╖│╔╖▌╡سâH╙╨ءO╡═╡─║ش┴┐╞س▓ى���ثش╡╜نm╛▀éغ╧ضّز╦╞╖│╔╖▌╡س║ش┴┐╞س▓ىءO┤ٍثذ╗ى╨╘│╔╖▌╞س▓ىءO┤ٍـr�ثش»ا╨د┐╔─▄╫╜ⁿ╙┌اoثر���ثش╢╝╩╟║ش┴┐▓╗╖√�����ةث╢°║ٍ╥╗╖N╟ل╨╬┼c│╔╖▌▓╗╖√╓«لg��ثش┐┤╦╞┤µ╘┌╨╘┘|╔╧╡─à^(qذ▒)e���ثش╞غî╓╗╩╟╥╗╝ê╓«╕َةث
╘┘▒╚╚ق����ثش╕∙ô■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ثش▒╗╬█╚╛╡─╦╞╖║═╫â┘|╡─╦╞╖╛∙î┘░┤╝┘╦╒ô╓«╟ل╨╬����ةث╚╗╢°ثش╘┌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��ثش╫â┘|╡─╦╞╖╚╘┴َ╘┌╝┘╦╓«┴╨��ثش╢°▒╗╬█╚╛╡─╦╞╖t▒╗أw╚ن┴╙╦╓«╓╨���ةث╚ق╣√╫╖û����ثشئل╩▓├┤╥زîت▒╗╬█╚╛╡─╦╞╖╒{╚ن┴╙╦ثش┐╔─▄╡─╗╪┤≡╩╟ث║╦╞╖▒╗╬█╚╛╓«╟░▒╛و╩╟╒µ╦���ثش╓╗╩╟╥ٌئل▒╗╬█╚╛╢°░l(fذة)╔·╫â╗»����ةث╥ٌ╢°�����ثش▀@╖N▒╗╬█╚╛╡─╦╞╖▓╗─▄▒╗╥╗╕┼╥ـئل╝┘╦�ثش╫≈ئل┴╙╦└و╜ظ╕ⁿ╝╙║╧▀mةث╡سûى}╩╟�ثش╫â┘|╡─╦╞╖═شء╙╚ق┤╦ةث╥ض╝┤���ثش╘┌ؤ]╙╨╫â┘|╓«╟░���ثش╦ⁿ╚╘╚╗╩╟╒µ╦ثش╫â┘|╓«║ٍ▓┼┐╔─▄░l(fذة)╔·│╔╖▌╗ٌ║ش┴┐╡─╫â╗»����ةث╥ٌ┤╦ثش║▄نy╒Jئل▀@╩╟îخâ╔╒▀à^(qذ▒)eîخ┤²╡─╒²«¤└و╙╔����ةث▀M╥╗▓╜┐╔╥╘╫╖û╡─╩╟�����ثش░┤╒╒╡┌98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ثش╦╞╖╚ق╣√╥ٌ▒╗╬█╚╛╢°╫â┘|��ثش╦ⁿ╡╜╡╫╩╟╝┘╦▀╩╟┴╙╦��ث┐╦╞╖▒╗╬█╚╛╡─║ٍ╣√▌^ئل╢ضء╙����ثش┐╔─▄╫â┘|ثش╥▓┐╔─▄ؤ]╙╨╫â┘|���ةث╦╞╖▒╗╬█╚╛╡س▓تؤ]╙╨░l(fذة)╔·╫â┘|╡─��ثشّزî┘┴╙╦╣╠اo╥╔û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╚ق╥ٌ▒╗╬█╚╛╢°░l(fذة)╔·│╔╖▌ثذ╠╪e╩╟╗ى╨╘│╔╖▌ثر╡─╫â╗»ـr�ثشّز╚ق║╬╒J╢ذ���ث┐îخ┤╦╖N╥(guذر)╖╢╕é║╧╡─╟ل╨╬�ثش┐╔─▄╨ك╥ز╜ظطî╒ô╔╧╡─▀M╥╗▓╜│╬╟فةث
╙╓▒╚╚ق��ثش░┤╒╒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│ش▀^╙╨╨د╞┌╡─╦╞╖î┘╙┌┴╙╦�ثش╢°╫â┘|╡─╦╞╖tّز▒╗╒J╢ذئل╝┘╦ةث─╟├┤��ثش│ش▀^╙╨╨د╞┌╡─╦╞╖┼c╫â┘|╦╞╖╩╟║╬╖NمP╧╡��ث┐╩┬î╔╧�ثش│ش▀^╙╨╨د╞┌╡─╦╞╖ثش╝╚┐╔─▄╫â┘|���ثش╥▓┐╔─▄╔╨╬┤╫â┘|�ةث╞غ╓╨�ثش│ش▀^╙╨╨د╞┌╡س╔╨╬┤╫â┘|╡─╦╞╖ثشّز▒╗╒J╢ذئل┴╙╦���ث╗╡س╩╟�����ثش│ش▀^╙╨╨د╞┌╟╥╫â┘|╡─╦╞╖����ثش╡╜╡╫î┘╙┌╝┘╦▀╩╟┴╙╦ث┐
┤╦═ظ�ثش╕∙ô■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ثشة░╔├╫╘╠و╝╙╖└╕»ر�����ةت▌o┴╧╡─╦╞╖ة▒╩╟┴╙╦�����ةث╡سûى}╩╟�ثش╔├╫╘╠و╝╙╖└╕»ر���ةت▌o┴╧╡─╨╨ئل��ثش╩╟╖ً┐╔─▄îد╓┬╦╞╖│╔╖▌╡─╫â╗»��ثش─╢°╩╣╠و╝╙║ٍ╡─╦╞╖│╔╖▌▓╗╖√║╧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�����ث┐╚ق╣√╩╟▀@ء╙���ثش╡╜╡╫î┘╙┌╝┘╦▀╩╟┴╙╦����ث┐
3.┐╔─▄╡─╜ظؤQ╦╝┬╖
╛C║╧╥╘╔╧����ثش╡┌98ùl╦∙┤_┴ت╡─╝┘╦┼c┴╙╦╖╢«بثش▓╗âH╘┌╕┼─ى╔╧┤µ╘┌╕é║╧مP╧╡�ثش╢°╟╥╘┌╞غ╦∙┴╨┼e╡─╛▀ٍwى╨═╔╧│╩شF│ِ╓T╢ض╗ه═شثش╞غ▀à╜ق▓ت╖╟╟ف╬·├≈┴╦�ةث▒M╣▄╢■╘ز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╡─┤_┴تثش╩╟╥╘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╞╜╨╨▓ت┴تئل▀ë▌ï╟░╠ط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─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╜ق╢ذو┐┤�����ثشàsاo╖ذ╡├│ِ╔╧╩ِ╜Y╒ô����ةث
╚ق╣√─î╢ذ╖ذ│ِ░l(fذة)�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┐╔╓^┤_┴ت┴╦┴╙╦╡─╥╗░ع╢ذ┴xةزةزة░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�ةث╢°╛═╡┌98ùl╦∙┤_┴ت╡─╦─╖N╝┘╦╢°╤╘ثش╛∙╘┌╥╗╢ذ╥ظ┴x║═│╠╢╚╔╧▀`╖┤┴╦╦╞╖ء╦£╩�����ثش╥ٌ╢°╢╝╘┌┴╙╦╖╢«ب╡─║ص¤z╖╢ç·╓«â╚�ةث╥ٌ┤╦ثش─▀@╥╗╥(guذر)╖╢│ِ░l(fذة)��ثش╝┘╦┼c┴╙╦▓ت╖╟╞╜╨╨▓ت┴ت╡─مP╧╡��ثش╢°╩╟î┘╖NمP╧╡�����ثش╝┘╦│╔ئل┴╙╦╡─╖N╕┼─ى���ةث
▀M╥╗▓╜╡╪ثش═ذ▀^│ل╧ٍ┐╔╓ز���ثش╡┌98ùl╥(guذر)╢ذ╡─╦─╖N╝┘╦╓«╦∙╥╘▓╗╖√║╧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�ثش╛∙╩╟┼c╠╪╢ذ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├▄╟╨╧ضمPةث╞غ╓╨��ثش╡┌ثذ1ثر╖N╟ل╨╬├≈┤_ⁿc├≈�ثش╦╞╖│╔╖▌┼c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▓╗╖√╡─ئل╝┘╦ثش▀@وù╥(guذر)╢ذئل║ٍ└m(xذ┤)╡─╖ذ░l(fذة)شF║═╕┼─ى╒√└و╠ط╣ر┴╦╛╦≈���ةثي@╚╗�ثش╡┌ثذ2ثر╖N╟ل╨╬╓╨╡─ة░╖╟╦╞╖├░│غ╦╞╖ة▒╝░╡┌ثذ3ثر╖N╟ل╨╬ة░╫â┘|╡─╦╞╖ة▒�ثش▒╪╚╗▓╗╖√║╧╠╪╢ذ╦╞╖ى╨═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ثش╢°╡┌ثذ2ثر╖N╟ل╨╬╓╨╡─ة░╥╘╦√╖N╦╞╖├░│غ┤╦╖N╦╞╖ة▒�ثش╚ق╣√▒╗└و╜ظئل╦╞╖ى╨═╢°╖╟╞╖┼╞╡─├░│غثش╥▓▒╪╚╗▓╗╖√║╧╠╪╢ذ╦╞╖ى╨═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��ةث╢°╚ق╣√îت▀@└ي╡─├░│غ└و╜ظئل╞╖┼╞╡─├░│غ�����ثشt╙╨┐╔─▄╘┌│╔╖▌╔╧┼c╠╪╢ذ╦╞╖ء╦£╩╥╗╓┬��ةث┤╦ـr����ثش▒M╣▄▀`╖┤┴╦╦╞╖ء╦╫R╡─╨╬╩╜ء╦£╩ثش╡سàs├ôنx╙┌╠╪╢ذ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▀@╥╗î┘|╥ز╟ٍ╓«═ظ���ةث▒╛╬─╒Jئل�ثش╡┌ثذ4ثر╖N╟ل╨╬╓«╦∙╥╘أw╙┌╝┘╦ثش╓≈╥ز╩╟ئل┴╦╖└╓╣îخ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╔·├ⁿ╖ذ╥µ╨╬│╔╬ثنU��ثش╢°▓╗╩╟╥ز▒ث╫o╧ضمP╕éب╞ٍءI(yذذ)╡─╜ؤإ·└√╥µ����ثش╗ٌ╩╟╬╝â╡─╩╨êِâَ╗»┼c╓╚╨ٌ╒√ىDةث╥ٌ┤╦�����ثشاo╒ô╩╟─î┘|╡─▒ث╫o─┐╡─│ِ░l(fذة)���ثش▀╩╟─╕┼─ى╚┌╪ئ┼cٍw╧╡àf╒{╡─╜╟╢╚┐╝┴┐��ثش╛∙ّز«¤╖ً╒J╔╧╩ِ╞╖┼╞├░│غ╡─╜ظطî╖╜░╕ث╗╡┌ثذ4ثر╖N╟ل╨╬ة░╦╞╖╦∙ء╦├≈╡─▀mّز░Y┼c╣خ─▄╓≈╓╬│ش│ِ╥(guذر)╢ذ╖╢ç·ة▒��ثش┐┤╔╧╚ح╩╟ء╦╫R▀`╖┤╨╬╩╜╥ز╟ٍ╡─ûى}�����ثش╡سîنH╔╧╚╘╩╟╥ٌئل╘ô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ءï│╔┼c╨╬╩╜ء╦╫Rثذء╦├≈╡─▀mّز░Y╗ٌ╣خ─▄╓≈╓╬ثر▓╗╖√╦∙╓┬�����ةث╛C╔╧╦∙╩ِثش╦∙╓^╝┘╦����ثش┐╔╥╘╘┌î┘|╔╧▒╗╜y╥╗░╤╬╒ئل┼c╠╪╢ذى╨═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ء╦£╩▓╗╖√╡─╦╞╖ةث
╚ق┤╦╥╗و�ثش┐╔îت╝┘╦╡─╥(guذر)╢ذ╥ـئل╠╪e╥(guذر)╖╢ثش╢°îت┴╙╦╡─╥(guذر)╢ذ╥ـئل╞╒═ذ╥(guذر)╖╢��ةث╘┌╔╧╩ِ╕é║╧╟ل╨╬╓╨���ثش╕∙ô■╠╪e╖ذâئ(yذصu)╙┌╞╒═ذ╖ذ╡─╖ذ└و����ثش┐╔╨╬│╔┤_╢ذ╡─▓├┼╨╜Y╒ô���ةث«¤╚╗�����ثش▀@ء╙╡─╜ظؤQ╖╜░╕�ثش╥▓┐╔─▄▀M╢°╥²░l(fذة)╨┬╡─╥╔ûث║╞غ╥╗�ثش▀@╖N└و╜ظ─╕∙▒╛╔╧═▀╜ظ┴╦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╢■╘ز▓ت┴ت─ث╩╜�����ثشâ╔╒▀╡─▀ë▌ïمP╧╡░l(fذة)╔·┴╦╓╪┤ٍ▐DôQ�����ث╗╞غ╢■�ثشئل┴╦╛S│╓â╔╒▀╡─▓ت┴تمP╧╡�ثش╛═▒╪وأîخ┴╙╦╖╢«ب▀M╨╨╧▐┐s╨╘└و╜ظثش╝┤▓╗╘┘îت╞غ└و╜ظئل╥╗░ع╨╘╡╪ة░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����ثش╢°╩╟╧▐┐s╡╪└و╜ظئلة░▓╗╖√║╧│╔╖▌ء╦£╩╓«═ظ╡─╞غ╦√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ةث╡س▀@ء╙╥╗و�ثش┴╙╦╫≈ئل╢╡╡╫╨╘╡─╞╒═ذ╥(guذر)╖╢╡─╣خ─▄╛═┐╔─▄▒╗╧≈╚ُةث╥ٌئل���ثش╝┘╦▓╔╚ة╡─╩╟┴╨┼e╩╜╡─┴ت╖ذ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��ثشنm╚╗╞غ╡┌ثذ1ثر╖N╟ل╨╬╛▀╙╨╠طىI╨╘╡─╥ظ┴xثش╡سàs╬┤▒╪─▄╝ق╪ô╥╗░عùl┐ى╡─╣خ─▄���ةث╡┌ثذ1ثر╖N╟ل╨╬è╒{╡─╩╟ة░╦╞╖│╔╖▌┼c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▓╗╖√ة▒�ثشاo╖ذ╕▓╔w║╦£╩╡─╦╞╖ء╦£╩╕▀╙┌ç°╝╥ء╦£╩╡─╟ل╨╬ةث┘|╤╘╓«�����ثش│╔╖▌╖√║╧ç°╝╥ء╦£╩╡سàs▓╗╖√║╧╦∙║╦£╩╡─╕ⁿ╕▀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╟ل╨╬�ثشاo╖ذ▒╗╝┘╦╓«╡┌ثذ1ثر╖N╟ل╨╬╦∙║ص¤zثش╡س╘ص╧╚┐╔─▄▒╗╝{╚ن┴╙╦╓«╡┌ثذ7ثر┐ىة░╞غ╦√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╓«╓╨��ةث╚ق╜ؤ╔╧╩ِ╧▐┐s╜ظطî╓«║ٍ���ثشtاo╖ذ╘┘▒╗┴╙╦╓«╡┌ثذ7ثر┐ى╦∙║ص╔w����ةثîخ║ٍ╥╗ûى}╢°╤╘��ثش╬┤و═ذ▀^îخ╝┘╦╡┌ثذ1ثر┐ى▀M╨╨╨▐╕─���ثش╝┤─ة░╦╞╖│╔╖▌┼c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▓╗╖√ة▒╕─ئلة░╦╞╖│╔╖▌┼c╦╞╖ء╦£╩▓╗╖√ة▒��ثش╝┤┐╔╪╡╫╜ظؤQ�����ةث
╧ض▌^╢°╤╘�����ثش╕ⁿئلمPµI╡─╩╟╟░╥╗ûى}�����ةث╚ق╣√─╝╚╙╨╥(guذر)╖╢ٍw╧╡│ِ░l(fذة)�ثش╥╘î╢ذ╖ذ╓╚╨ٌئل╣ج╫≈╟░╠طثشîت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مP╧╡╫≈╖Nî┘مP╧╡╡─╢ذ╬╗╚╘╛▀╙╨╒√ٍw╡─║╧└و╨╘����ةث╞غ▓╗╡س▓╗ـ■╨╬│╔┤ٍ╡─╠┴P┬ر╢┤ثش╢°╟╥╘┌░l(fذة)╔·╕é║╧╡─╟ل╨╬╓╨�����ثش┐╔═ذ▀^╧ضمP╡─╕é║╧╖ذ└و╡├│ِ┤_╢ذ╟╥═╫«¤╡─╜Y╒ô����ةث╡س╩╟ثش▀@╥╗╕é║╧مP╧╡▒و├≈��ثش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╢■╘ز▓ت┴ت─ث╩╜╓╡╡├╒J╒µ╖┤╦╝ةث╘┌╬┤و╡─╨▐╖ذ╖╜░╕╔╧���ثش╕ⁿئل║╧└و╡─╖╓ى╥(guذر)╓╞─ث╩╜┐╔─▄╩╟ث║╩╫╧╚ثش╘┌╒√ٍw╔╧îت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╥(guذر)╓╞îخ╧ٍ╢ذ╬╗ئلة░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��ةث╞غ┤╬����ثشة░▓╗╖√║╧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┐╔à^(qذ▒)╖╓ئلة░▓╗╖√║╧╨╬╩╜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┼cة░▓╗╖√║╧î┘|ء╦£╩╡─╦╞╖ة▒ةث╞غ╓╨��ثش▓╗╖√║╧╨╬╩╜ء╦£╩�����ثش╩╟╓╕╘┌╦╞╖├√╖Q�����ةت╠╪╩ظء╦╫R���ةت░ⁿ╤b═ظ╙^╡╚╖╜├µ▓╗╖√║╧╧ضمP╦╞╖ء╦£╩��ث╗▓╗╖√║╧î┘|ء╦£╩�ثش╩╟╓╕╘┌╦╞╖╡─│╔╖▌╝░╛▀ٍw║ش┴┐╔╧▓╗╖√║╧╧ضمPء╦£╩ةث▀M╥╗▓╜╡╪��ثش┐╔îخ╦╞╖╡─╙╨╨د│╔╖▌ثذ╗ى╨╘│╔╖▌ثر┼c╕╜╝╙│╔╖▌▀M╨╨à^(qذ▒)╖╓�����ثش═شـrطءîخ▓╗═شى╨═│╔╖▌╡─╛▀ٍw║ش┴┐╝░╞غ╞سنx╢╚▀M╨╨╕ⁿ╛س╝أ╡─┐╝┴┐�ةث
╢■ةت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╖╓نx┼c╝â╗»ث║
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
╝░╞غîشF
╨╨ئل┐═ٍw│╨▌d╡─╩╟îخ╠╪╢ذ╖ذ╥µ╡─▒ث╫o����ةثîخ╦╞╖╖╕╫ي╓╨╨╨ئل┐═ٍw╡─╒{╒√ثشî┘|╔╧╘┤╙┌îخ╧ضمP╥(guذر)╖╢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╓╪╨┬└و╜ظ┼c╢ذ╬╗��ةث╥ٌ┤╦�ثش╙╨▒╪╥ز┤╠╞╞╨╨ئل┐═ٍw╡─├µ╝ثش╒J╒µî╥ـ║═╖┤╦╝┤╦┤╬╨╠╖ذ╨▐╒²▒│║ٍ╒µ╒²╡─╥(guذر)╖╢╥ظ╓╝╦∙╘┌�����ةث
ثذ╥╗ثر╖ذ╥µ╫Reث║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╓«ب
2011─م╡─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���ثش╚ة╧√┴╦╔·«a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╓╨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╓«╥ز╟ٍ��ثش╩╣╘ô╫ي▓╗╘┘▒╗╥ـئل╛▀ٍw╬ثنU╖╕�����ةث╞غ║ٍثشîW╜قç·└@╞غ╛┐╛╣╧╡╨╨ئل╖╕▀╩╟│ل╧ٍ╬ثنU╖╕╒╣ل_ب╒ô����ةث▀@╥╗ب╒ô╡─╜╣ⁿc╘┌╙┌ثش╔·«a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╡─│╔┴ت╛┐╛╣╩╟âH╨ك╥ز╔·«a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╡─╨╨ئل����ثش▀╩╟╨ك╥ز╥╗╖N──┼┬╩╟│ل╧ٍ╡─╖ذ╥µ╟╓║خيLنUث┐ّز«¤│╨╒J��ثش╨╨ئل╖╕┼c│ل╧ٍ╬ثنU╖╕╡─╛ضنx═∙═∙╩╟╥╗╝ê╓«╕َ��ةث╨╨ئل╖╕╚ق╣√▒╗╫≈ئل╨╬╩╜╖╕و└و╜ظ���ثش╞غ┼c╖ذ╥µ╟╓║خ╡─مP┬ô╨╘╛═ـ■▒╗╟╨¤ض�ثش▀@╥╗╖╕╫ي╨╬ّB(tذجi)╡─╒²«¤╨╘╥▓îتéغ╩▄┘|╥╔ث╗╢°╚ق╣√╚╘îت╞غ╫≈ئلî┘|╖╕وîخ┤²�����ثش╒Jئل╨╨ئل╡─╖ذ╥µ╟╓║خ╠╪╒≈▓╗┐╔╖┼ùë��ثش─╟├┤����ثش╧┬╩ِ╥╔û▒عنy╥╘▒▄├ظث║╨╨ئل╖╕╦∙╘ه│╔╡─╖ذ╥µ╬ثنU┼c│ل╧ٍ╬ثنU╓«لgّز╚ق║╬à^(qذ▒)╖╓ث┐┐╔─▄╡─╗╪┤≡╩╟���ثش╟░╒▀╩╟╥╗╖N¤M╓╞╡─╬ثنU���ثش▓╗╘╩╘S╥╘╖┤╫C╝╙╥╘═╞╖صث╗║ٍ╒▀t╩╟─│╖N═╞╢ذ╡─╬ثنU��ثش┐╔╥╘═ذ▀^╖┤╫Cو═╞╖صîخ│ل╧ٍ╬ثنU╡─═╞╢ذ��ةث
╢°╘┌▒╛╬─┐┤و�ثش╔·«a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╛┐╛╣╧╡╨╨ئل╖╕▀╩╟│ل╧ٍ╬ثنU╖╕╡─ب╒ô���ثش╞غ╟░╠ط╘┌╙┌▒╛╫ي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├≈┤_�����ةث╦∙╓^¤M╓╞╬ثنU╗ٌ│ل╧ٍ╬ثنU╡─║ظ┴┐���ثش▒╪وأ╥╘╞غ╛▀ٍw╓╕╧ٌ╡─╫Reئل╟░╠ط��ةث╥ض╝┤ثش╩╟îخ║╬╖N╖ذ╥µ╘ه│╔═■├{�ث┐╖ذ╥µى╨═▓╗═شثش╞غ╖ذ╥µمP┬ô╨╘╡─╥ز╟ٍ┼c▒وشF╨╬╩╜╥ض┐╔─▄╙╨╦∙à^(qذ▒)e��ةث╘¤╤╘╓«�ثش╚ق╣√▒╛╫ي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╩╟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ثش─╟├┤����ثش╔·«aةتغN╩█╝┘╦╡─╨╨ئل▒╛╔و▒ع╫ع╥╘ءï│╔îخ╓╚╨ٌ╓«▀`╖┤��ثش▓ت╥╤╘ه│╔îخ╓╚╨ٌ╖ذ╥µ╓«î║خ�����ةثîخ▒╛╛═│ل╧ٍ╡─╓╚╨ٌ╖ذ╥µ╢°╤╘ثشنy╥╘╧ن╧ٍة░│ل╧ٍ╨╘╡─نp╓╪»B╝╙ة▒�����ثش╝┤îخ│ل╧ٍ╖ذ╥µ╘┘╘O╓├│ل╧ٍيLنU╖╕�����ث╗╢°╚ق╣√▒╛╫ي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▓ت╖╟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����ثش╢°╩╟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��ثش─╟├┤�ثش╘┌┴ت╖ذ╨╬│╔╔╧îخ╖ذ╥µمP┬ô╨╘╡─╥ز╟ٍثش╛═╝╚┐╔─▄╩╟îخ▀@╥╗╖ذ╥µ╡─╛▀ٍw╬ثنU�ثش╥▓┐╔─▄âH╥ز╟ٍ│ل╧ٍ╬ثنUثش▓ت╘╩╘S═ذ▀^╛▀ٍw��ةتî┘|╬ثنU╡─╟╖╚▒و═╞╖ص┤╦╖N│ل╧ٍ╬ثنU╡─┤µ╘┌�����ثش╥ض┐╔─▄╥ز╟ٍî║خ╜Y╣√╡─░l(fذة)╔·ث╗▀M╥╗▓╜╡╪�����ثش╚ق╣√▒╛╫ي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╩╟═║╧╖ذ╥µ�ثش╝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┼c╣س▒è╜ة┐╡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╡─╜Y║╧�ثش─╟├┤ثش╛═┐╔─▄îخ▀@â╔╖N▓╗═ش╖ذ╥µى╨═╖╓e╥ز╟ٍ▓╗═ش╡─╖ذ╥µ╟╓║خمP┬ô�ةث╛═┤╦╢°╤╘ثش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╡─╨▐╕─┐╔─▄âHâH╩╟├≈┤_┴╦�����ثشîخ╙┌╙├╦╒▀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�����ثش▒╛╫ي▓ت▓╗╥ز╟ٍ╛▀ٍw╬ثنU╡─│╔┴ت��ةث
▀@ء╙╥╗و�ثش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├≈┤_ثشî╛▀╙╨مPµI╥ظ┴x���ةث▀@╖N╥ظ┴x╘┌مّ╙┬░╕░l(fذة)╔·╓«║ٍ�ثش╕ⁿ╩╟╘╜░l(fذة)═╣ي@│ِو�����ةثمّ╙┬╘┌ؤ]╙╨╚ة╡├▀M┐┌┼·╬─╡─╟لؤr╧┬����ثش─╙ة╢╚┘▀M╚≡╩┐ة░╕ً┴╨╨l(wذذi)ة▒╡─╖┬╓╞╦ةث░┤╒╒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╓«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╥└╖ذ▒╪وأ┼·£╩╢°╬┤╜ؤ┼·£╩▀M┐┌╡─╦╞╖���ثش░┤╝┘╦╒ô�ةث▒و├µ╔╧┐┤����ثشمّ╙┬░╕╡─ب╒ô╓≈╥زç·└@▀@╥╗╬┤╜ؤ┼·£╩╢°▀M┐┌╡─╦╞╖╩╟╖ًءï│╔╝┘╦╢°╒╣ل_ثش▀M╢°╤╙╔ه╡╜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╝┘╦╖╢«ب╡─║╧└و╨╘ةت╨╠╖ذ┼c╟░╓├╖ذ╘┌╝┘╦╒J╢ذ╡─╥└─مP╧╡╡╚ûى}╓«╔╧����ةث╡سîنH╔╧ثش╨╨ئل┐═ٍw╡─═ظ╤╙┤_╢ذ╥▓║├��ثش╖ذ╥µيLنU╨╘┘|╡─└و╜ظ╥▓║├��ثش╘┌╕∙╡╫╔╧╩╟╙╔▒╛ùl╡─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╝░╞غ╦∙إ╢ذ╡─╥(guذر)╖╢▒ث╫o╖╢ç·╦∙ؤQ╢ذ╡─���ةث╘┌╝╚╙╨╡─╜ظؤQ╖╜░╕╓╨����ثشاo╒ô╩╟═ذ▀^î┘|╜ظطî╡─╖╜╩╜و╧▐┐s╝┘╦╡─â╚║ص�����ثش▀╩╟═ذ▀^│ل╧ٍ╬ثنU╖╕╡─╖┤╫Cول_▒┘│ِ╫ي╗»╡─═╛╜�����ثش╢╝▒╪وأ╗╪أw╡╜îخ▒╛╫ي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î╔≈╦╝┐╝╓«╔╧�����ةث
╘┌═ذ╒f┐┤و���ثش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ئل═نs┐═ٍw�����ثش╝╚▒ث╫oç°╝╥╡─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��ثش╙╓▒ث╫o├ً▒è╡─╔وٍw╜ة┐╡║═╔·├ⁿ░▓╚سةث╡س╘┌مّ╙┬░╕╓╨�����ثشâ╔╖N╖ذ╥µ╡─▒ث╫o╓«لg│ِشF┴╦─│╖Nâ╚╘┌╡─╛oê┼cؤ_═╗مP╧╡���ةث╥ض╝┤��ثش╬┤╜ؤ┼·£╩╝┤▀M┐┌▒M╣▄▀`╖┤┴╦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���ثش╡سîخ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àsؤ]╙╨╨╬│╔╛▀ٍwôp║خ�����ثش╔ُ╓┴ـ■«a╔·╒²├µ╓·╥µ�ةث╗∙╙┌î┘|╡─═╫«¤╨╘┐╝ّ]���ثشئلîشF╔╧╩ِ╟ل╨╬╡─│ِ╫ي╗»╠└و��ثش╥╗╖N▌^ؤQ╜^╡─╖╜░╕╩╟���ثش╪╡╫═╞╖ص═ذ╒fثش╒Jئل╔·«a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▒ث╫o╡─╖ذ╥µâHâH╩╟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┼c╔·├ⁿ░▓╚سثش▓ت▓╗░ⁿ└ذç°╝╥╡─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���ةث╥ٌ┤╦ثشîخ╙┌âHâH╟╓╖╕┴╦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����ثشàsîخ├ً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░▓╚سؤ]╙╨î┘|╬ث║خ┐╔─▄╨╘╡─╟ل╨╬ثش▓╗ّز«¤╒J╢ذئل╖╕╫ي���ث╗┴و╥╗╖N▌^£╪║═╡─╖╜░╕t╩╟�ثش╚╘╛S│╓═ذ╒f╓╨═نs┐═ٍw╡─╗∙▒╛╢ذ╬╗����ثش╡س╘çêDîخ╕≈╛▀ٍw╖ذ╥µلg╡─╜YءïمP╧╡╙ك╥╘╓╪╨┬مUطîةث╘┌┤╦╖N╙^ⁿc┐┤و�ثش▒╛╫ي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╝╚░ⁿ║شç°╝╥╡─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ثش╥▓░ⁿ║ش▓╗╠╪╢ذ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░▓╚س�ةث╡س╩╟ثش╟░╒▀ئل┤╬╥ز╖ذ╥µ����ثش║ٍ╒▀ئل╓≈╥ز╖ذ╥µثش║ٍ╒▀╡─╬╗نA╕▀╙┌╟░╒▀���ةث«¤╢■╒▀░l(fذة)╔·ؤ_═╗ـr��ثشّز╥╘▒ث╫o║ٍ╒▀ئلâئ(yذصu)╧╚�ةثîخ─╟╨رâH╟╓║خ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àsîخ├ً▒è╡─╔وٍw╜ة┐╡اo║خ╔ُ╓┴╙╨╥µ╡─╨╨ئلثش▓╗ّز«¤╒J╢ذئل╖╕╫ي���ةث┼c╔╧╩ِâ╔╖N╖╜░╕╧ضîخّز���ثشاo╒ô╩╟îت▒╛╫ي╖ذ╥µ└و╜ظئل╬╝â╡─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╙^ⁿcثش▀╩╟îت▒╛╫ي╖ذ╥µ└و╜ظئل═║╧╖ذ╥µ╡س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ئل╓≈╥ز╖ذ╥µ╡─╙^ⁿc��ثش╢╝ـ■╘┌╔╧╩ِ╟ل╨╬╓╨╡├│ِ╙╨╫ي╡─╜Y╒ô����ةث
╙╔┤╦ثشîخ▒╛╫ي╛▀ٍw╖ذ╥µى╨═╡─╫Re�����ثش╥╘╝░îخ╖ذ╥µلg╜YءïمP╧╡╡─═╫«¤░╤╬╒��ثش╛═│╔ئل╫ٍ╙╥┼╨¤ض╡─مPµI╦∙╘┌����ةث┘|╤╘╓«�����ثش▒╪وأ╓▒├µ╧┬╩ِûى}ث║▒╛╫ي▒ث╫o╡─╡╜╡╫╩╟╬زأ╖ذ╥µ▀╩╟═║╧╖ذ╥µث┐╚ق╣√╩╟╬زأ╖ذ╥µ���ثش▀@╖N╖ذ╥µ╩╟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���ثش▀╩╟▓╗╠╪╢ذ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┼c╔·├ⁿ░▓╚س����ث┐╚ق╣√╩╟═║╧╖ذ╥µثشâ╔╖N╖ذ╥µ╓«لg╛┐╛╣╩╟╩▓├┤مP╧╡��ث┐╩╟▓ت┴╨مP╧╡▀╩╟╬╗نAمP╧╡���ث┐╚ق╣√╩╟╬╗نAمP╧╡����ثشâ╔╖N╖ذ╥µ╡╜╡╫╩ن╓≈╩ن┤╬��ث┐«¤╢■╒▀لg░l(fذة)╔·ؤ_═╗ـr����ثشّزîخ║╬╖N╖ذ╥µ╙ك╥╘âئ(yذصu)╧╚▒ث╫o����ث┐
ثذ╢■ثر╖ذ╥µâنxث║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╝░╞غîشF
1.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╖ذ╥µ╗ه═ش┼c╖ذ╥µ╖╓┴ت
îخ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╡─╖ذ╥µ╫Re�ثش▒╪وأ╥╘╘ô╥(guذر)╖╢╫≈ئل│ِ░l(fذة)ⁿc┼c┼╨¤ض╥└ô■ةثي@╚╗�ثش╘┌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╓«╓╨ثش╝┘╦╫≈ئل╔·«a┼cغN╩█╡─îخ╧ٍ����ثش╩╟╬╥éâ═╕╬ِ║═░╤╬╒╞غ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▒╪╥ز╓╨╜لثش▀@╥▓╖√║╧╨╨ئل┐═ٍw╫≈ئل▒ث╫o┐═ٍw╓«▌dٍw╡─╗∙▒╛╘ص└و�ةث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╓╨├≈┤_╥(guذر)╢ذ�ثشة░▒╛ùl╦∙╖Q╝┘╦ثش╩╟╓╕╥└╒╒ة╢╓╨╚A╚╦├ً╣▓║═ç°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╥(guذر)╢ذî┘╙┌╝┘╦║═░┤╝┘╦╠└و╡─╦╞╖�����ةت╖╟╦╞╖ة▒����ةث╕∙ô■▀@╥╗╓╕╩╛ثش╨╠╖ذ╔╧╝┘╦╡─╒J╢ذ�����ثشîنH╔╧═م╚س╥└─╙┌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ثش│╔ئل╥╗╖N╟░╓├╖ذ╡─ة░╕┼─ى╨╘╕╜╙╣ة▒����ةث
ûى}╘┌╙┌��ثش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╨╡─ة░╝┘╦ة▒╕┼─ى╩╟╥╗éة░نsَ█╬ية▒��ةث╘ô╖ذ╡┌48ùlîخ╝┘╦╡─├ك╩ِ��ثش▓╔╚ة┴╦ة░2+6ة▒─ث╩╜�����ةث╟░2╖Nئل╝┘╦╡─╥╗░ع╟ل╨╬ثذ▒╛و╡─╝┘╦ثر��ثش║ٍ6╖Ntئل░┤╝┘╦╒ôثذ¤M╓╞╡─╝┘╦ثر╡─╟ل╨╬��ةث╔╧╩ِ░╦╖N╟ل╨╬îنH╔╧┐╔▒╗╖╓ئلâ╔ىث║╥╗ى╩╟����ثش░┤╝┘╦╒ô╡─╡┌ثذ1ثرثذ2ثرثذ5ثر╚²╖N╟ل╨╬ثش╝┤ة░ç°╒╘║╦╞╖▒O(jiذةn)╢╜╣▄└و▓┐لT╥(guذر)╢ذ╜√╓╣╩╣╙├╡─ة▒ة░╥└╒╒▒╛╖ذ▒╪وأ┼·£╩╢°╬┤╜ؤ┼·£╩╔·«a�ةت▀M┐┌����ثش╗ٌ╒▀╥└╒╒▒╛╖ذ▒╪وأآzٌئ╢°╬┤╜ؤآzٌئ╝┤غN╩█╡─ة▒╝░ة░╩╣╙├╥└╒╒▒╛╖ذ▒╪وأ╚ة╡├┼·£╩╬─╠û╢°╬┤╚ة╡├┼·£╩╬─╠û╡─╘ص┴╧╦╔·«a╡─ة▒����ةث╦ⁿéâ├≈ي@╛▀╙╨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╠╪╒≈ثشàs▓╗╥╗╢ذîخ╙├╦╒▀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╘ه│╔═■├{�����ةث┴و╥╗ى╩╟��ثشâ╔╖N╝┘╦╡─╥╗░ع╟ل╨╬╝░░┤╝┘╦╒ô╓╨╡─╡┌ثذ3ثرثذ4ثرثذ6ثر╖N╟ل╨╬�����ثش╝┤ة░╦╞╖╦∙║ش│╔╖▌┼c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╥(guذر)╢ذ╡─│╔╖▌▓╗╖√╡─ة▒ة░╥╘╖╟╦╞╖├░│غ╦╞╖╗ٌ╒▀╥╘╦√╖N╦╞╖├░│غ┤╦╖N╦╞╖╡─ة▒ة░╫â┘|╡─ة▒ة░▒╗╬█╚╛╡─ة▒ة░╦∙ء╦├≈╡─▀mّز░Y╗ٌ╒▀╣خ─▄╓≈╓╬│ش│ِ╥(guذر)╢ذ╖╢ç·╡─ة▒╡╚╟ل╨╬����ةث╦ⁿéâ╛∙┐╔─▄╔µ╝░╦╞╖│╔╖▌╡─╫â╗»┼c▓╗╖√ثش─╢°£pôp╦╞╖╡─îنH»ا╨د╗ٌ╩╟îخ╗╝╒▀╜ة┐╡«a╔·╕▒╫≈╙├ةث╘┌▀@╨ر╟ل╨╬╧┬����ثش╦∙▒ث╫o╡─╖ذ╥µ╩╟╕╜╓°╙┌╦╞╖│╔╖▌╓«╔╧╡─╜ة┐╡┼c╔·├ⁿ░▓╚سثش╢°╖╟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▒╛╔و�����ةث
«¤╚╗���ثش╔╧╩ِâ╔╖N╖ذ╥µ▓ت╖╟═م╚س¤ض┴╤╡─مP╧╡���ةث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╬│╔��ثش▓┐╖╓╩╟ئل┴╦▒ث╫o╗╝╒▀╡─╙├╦░▓╚س��ةثمP╙┌┤╦ⁿc�ثش╬╥ç°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ùl╝┤ل_╫┌├≈┴xث║ة░ئل┴╦╝╙è╦╞╖╣▄└وثش▒ث╫C╦╞╖┘|┴┐��ثش▒ث╒╧╣س▒è╙├╦░▓╚س║═║╧╖ذآض╥µ���ثش▒ث╫o║═┤┘▀M╣س▒è╜ة┐╡���ثش╓╞╢ذ▒╛╖ذ��ة���ثة▒╕∙ô■▀@ùl╥(guذر)╖╢ثش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╬│╔┼c╛S│╓����ثش╓╗╩╟─│╖N╩╓╢╬ثش╞غ╜KءO─┐╡─╘┌╙┌▒ث╒╧╣س▒è╡─╙├╦░▓╚س��ثش▒ث╫o║═┤┘▀M╣س▒è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ث╚╗╢°���ثش▓ت▓╗─▄╥ٌئلâ╔╒▀┤µ╘┌╩╓╢╬┼c─┐╡─╓«مP╧╡�ثش▒ع╖ً╒J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╛▀╙╨╧ضîخزأ┴ت╡─╞╖╕ً��ثش▓ت▀M╢°╖ً╒J╞غà^(qذ▒)╖╓╙┌╣س▒è╜ة┐╡╡─زأ┴ت╖ذ╥µ╡╪╬╗�ةث┘|╤╘╓«ثش▓╗─▄îت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╧√فَ╘┌îخ╣س▒è╜ة┐╡╡─مP╟╨╓«╓╨�����ةث╓«╦∙╥╘╚ق┤╦ثش╓≈╥ز╩╟╗∙╙┌â╔ⁿc└و╙╔�����ةث
╞غ╥╗����ثش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نm╚╗╘┌╙╨╨ر╟ل╨╬╧┬╩╟ئل┴╦╛S╫o╙├╦░▓╚سثش╡س▓ت╖╟┐é╩╟┐╔╥╘▒╗▀╘ص╡╜░▓╚س└√╥µ╓«╔╧�ثشâH╫≈ئل╞غ╖┤╔غ╨╘╨د╣√و└و╜ظةث└²╚ق��ثش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3ùl╥(guذر)╢ذ�ثشة░╜ذ┴ت┐╞îW���ةتç└╕ً╡─▒O(jiذةn)╢╜╣▄└و╓╞╢╚���ثش╚س├µ╠ط╔²╦╞╖┘|┴┐ثش▒ث╒╧╦╞╖╡─░▓╚س�����ةت╙╨╨دةت┐╔╝░ة▒�ةث╞غ╓╨╡─┐╔╝░╨╘└√╥µي@╚╗┼c░▓╚س└√╥µ┤µ╘┌à^(qذ▒)╕َثشءï│╔─│╖Nزأ┴ت╡─╓╞╢╚─┐╡─╗ٌ└√╥µ╘V╟ٍ�����ةث
╞غ╢■��ثش╝┤╩╣╘┌â╔╒▀╛▀╙╨╥╗╢ذ╙│╔غمP╧╡ـr��ثش╥▓ّز╛S│╓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╫≈ئل╣س▒è╜ة┐╡╖ذ╥µ╡─╫كôُî╙╡╪╬╗�����ثش╢°▓╗▌p╥╫┤╠╞╞�����ةث▀@▓╗âH╩╟╥ٌئل�����ثش╞╞ë─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╨ئل╛▀╙╨îخ╣س▒è╜ة┐╡░▓╚س╡─ى╨═╨╘╬ثنU��ثش╥ٌ╢°╨ك╥ز╠ط╟░╙ك╥╘┐╣╓╞║═╢ٍأت�ث╗╥▓▓╗âH╩╟╥ٌئل���ثش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╩╟╣س▒è╡├╥╘شFî╓د┼غ╞غ░▓╚س╖ذ╥µ╡─═ظ╘┌▒ث╒╧ثش╞غ╫≈ئل╣س▒è╜ة┐╡╖ذ╥µ░▓╨─╨╨╩╣╡─═ظ╘┌ùl╝■╢°╡├╥╘╛S╫o���ث╗╕ⁿئل╓╪╥ز╡─╩╟����ثش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╛▀╙╨╛S│╓═╫«¤╡─╨╨ئل─ث╩╜▀M╢°╖(wذدn)╣╠╔قـ■ىA╞┌�ةتè╗»╥(guذر)╖╢╥ظ╫R╡─آC─▄ةث▀@╖NآC─▄▒M╣▄╥ٌ╞غ▒ث╒╧╡╪╬╗╢°╔·���ثش╡سàs╛▀╙╨─│╖N╫╘╜M┐ù���ةت╫╘è╗»╡─âA╧ٌةث╛═╔قـ■╧╡╜y╡─╖╓╗»╢°╤╘���ثش▀@╖N╥(guذر)╖╢╨╘╡─╛S│╓┼cè╗»�����ثش╛▀╙╨╣▓═شٍw╦▄╘ه╡─╫╘╘┌╨╘âr╓╡ةث╙╔┤╦�ثش╦ⁿ┐╔─▄س@╡├│ش╘╜╙┌╣س▒è╜ة┐╡╓«╤╙╔ه╗ٌ═╢╔غ╡─╥ظ┴x����ثش╢°╝╙╥╘زأ┴ت╡─╒²«¤╗»�ةث
ّز«¤│╨╒Jثش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مP╙┌╝┘┴╙╦╥(guذر)╢ذ╡─╕∙▒╛╚▒╧▌╘┌╙┌���ثشîت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┼c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╖ذ╥µ▓╗╟ة«¤╡╪╗ه═ش��ثش▓ت═ذ▀^╦∙╓^ة░░┤╝┘╦╒ôة▒ة░░┤┴╙╦╒ôة▒╡─¤M╓╞╨╘╤b╓├�����ثش╔·╙▓╡╪îت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▀@╥╗╖ذ╥µ╚√╚ن╞غ╓╨���ةث╒²╩╟┐┤╡╜┴╦▀@â╔╖N╖ذ╥µلg╡─à^(qذ▒)╕َâr╓╡�ثش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îخ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▀M╨╨┴╦╜Yءï╨╘╒{╒√���ةث▀@╥╗╒{╒√╡─╓╪ⁿc��ثش╝┤╩╟îخة░░┤╝┘╦╒ôة▒ة░░┤┴╙╦╒ôة▒╓╨î┘╙┌╬╝â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╘┘|╡─╨╨ئل���ثش─╝┘┴╙╦╡─╖╢«ب╓╨┼┼│²│ِ╚ح��ثش▓ت╘ِ╘O╨┬╡─زأ┴ت╥(guذر)╖╢╝╙╥╘╥(guذر)╓╞��ةث╥▓╝┤���ثش═ذ▀^╨┬╖ذ╡┌98ùl╝┘╦ةت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ùl┐ى�����ثشîخ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╡┌48ùl����ةت╡┌49ùl╝╙╥╘╨▐╒²║═╓╪╨┬╒√║╧ثش═شـr���ثشîت╘صو¤M╓╞╨═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¤M╓╞╨═┴╙╦╓╨╡─▓┐╖╓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┼▓╓┴╡┌124ùl╝╙╥╘╬زأ╥(guذر)╓╞�ةث┤╦╖N┼ش┴خثش╩╣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┼c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▀@â╔╖N╖ذ╥µ▒╗╧ضîخ╟ف╬·╡╪âنxل_و�����ثش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╕┼─ىâ╚║ص┼c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╥ضي@╡├╕ⁿئل╝â╗»�ةث
2.نp╓╪╖ذ╥µ╒ô╝░╞غûى}╦∙╘┌
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╨┬╘Oثش╥▓ّز▒╗╓├╚ن╔╧╩ِ▒│╛░╓╨و└و╜ظ║═░╤╬╒�ةث╗∙╙┌╘ص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╓«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�ثش╨╠╖ذ╔╧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╒J╢ذ��ثشîخ╟░╓├╖ذ╛▀╙╨è╓╞╨╘╡─╥└╕╜مP╧╡�ةث╙╔┤╦ثش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╕┼─ى╗ه═ش�����ثش▌▒╪▀Bد╡╪╥²░l(fذة)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╡─â╚▓┐╖ذ╥µؤ_═╗���ثش▀@╘┌مّ╙┬░╕╓╨▒وشF╡├╙╚ئل├≈ي@�����ةثئل╗»╜ظ╔╧╩ِؤ_═╗▓تس@╡├═╫«¤╜Y╒ô�ثش╙╨îW╒▀▓╗╡├▓╗═ذ▀^ة░نp╓╪╖ذ╥µ╒ôة▒وî┘|╗»╡╪╧▐┐s▒╛╫ي╡─╠┴P╖╢ç·�ةث╛▀ٍw╢°╤╘ثش▀@╖N╖╜░╕╩╫╧╚│╨╒J▒╛╫ي╡─═║╧╖ذ╥µ╠╪╒≈��ثش╡س═ذ▀^îخ╖ذ╥µلgمP╧╡╡─╓╪╨┬مUطî�ثشو╒ô╫C╣س▒è╜ة┐╡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╓«╙┌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âئ(yذصu)╘╜╡╪╬╗�ثش▀M╢°╘┌âH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س╬┤îخ╣س▒è╜ة┐╡ةت╔·├ⁿ╘ه│╔î┘|╟╓║خ╡─êِ║╧���ثش╡├│ِاo╫ي╡─╜Y╒ô��ةث
╚╗╢°���ثش╚ق╣√│╨╒J▀@╖Nة░نp╓╪╖ذ╥µ╒ôة▒ثش╛═┐╔─▄دو╚ق╧┬ûى}ةث
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ثش╖ذ╥µ╜Yءï╡─╒`╒J���ةث╚ق╣√╒Jئل▒╛╫ي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ئلنp╓╪╖ذ╥µ�����ثش─╟├┤�ثش▀@â╔╖N╖ذ╥µ╓«لg╡╜╡╫╩╟║╬مP╧╡ث┐ي@╚╗��ثشâ╔╖N╖ذ╥µ╓«لg▓ت╖╟ôً╥╗مP╧╡�ثش╢°╩╟²RéغمP╧╡ةثôQ╤╘╓«�ثش▓ت▓╗╩╟╨╨ئل╟╓╖╕╞غ╓╨╡─╚╬║╬╥╗╖N╖ذ╥µثش╝┤▒ع╩╟╓≈╥ز╖ذ╥µ��ثش╝┤┐╔│╔┴ت╖ذ╥µ╟╓║خ�ةث╧ض╖┤ثش╨╨ئل▒╪وأ═شـr╟╓║خâ╔╖N╖ذ╥µ�ثش╖╜─▄╛▀éغ▒╛╫ي╡─╖ذ╥µ╟╓║خ╨╘ةث╚╗╢°���ثش╘┌╔╧╩ِنp╓╪╖ذ╥µ╒f╡─╒ô╫C╓╨����ثش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س╬┤î┘|╨╘╟╓╖╕╣س▒è╜ة┐╡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╡─╨╨ئل╓«╦∙╥╘اo╫ي�ثش╩╟╗∙╙┌║ٍ╥╗╖ذ╥µ╓«╙┌╟░╥╗╖ذ╥µ╡─âئ(yذصu)╘╜╡╪╬╗╢°îد│ِةث▀@╘┌▀ë▌ï╔╧║ِ┬╘┴╦â╔╖N╖ذ╥µ▒╪وأ╝µ╛▀╡─مP╧╡��ثش╢°ن[╚╗îتâ╔╒▀╓├╚ن╥╗╖N▒╦┤╦ؤ_═╗���ةت╧ض╗ح║ظ┴┐╡─مP╧╡╓«╓╨���ةث▀M╥╗▓╜╡╪ثش╓«╦∙╥╘╥زîت║ٍ╒▀╓├╙┌âئ(yذصu)╘╜╙┌╟░╒▀╡─╬╗╓├��ثشt╩╟ئل╘┌╧ض╗حؤ_═╗╡─╟لؤr╧┬îخ╟░╒▀╙ك╥╘╧▐╓╞╗ٌ┼┼│²îج╟ٍ╒²«¤╗»╕∙ô■���ةث╢°╩┬î╔╧����ثش═║╧╖ذ╥µ╩╟╥╗╖N²Réغ╨╘╜Yءï���ةث╛═╩╟╖ً▒╪وأ▒╗╟╓║خ╢°╤╘�����ثشâ╔╖N╖ذ╥µî╛▀╙╨═ش╡╚╡╪╬╗����ث╗╛═┼╨¤ض╬╗╨ٌ╢°╤╘ثش╥▓اo╦∙╓^╟░║ٍ╓«╖╓����ةث╝┤╩╣┤µ╘┌╓≈���ةت┤╬╖ذ╥µ╓«╖╓����ثش╥▓╓╗╩╟╛═â╔╖N╖ذ╥µ╓«لg╡─╓╪╥ز╨╘╙ك╥╘â╚▓┐▒╚▌^╡─╜Y╣√�����ثش╦ⁿ╜^▓╗╥ظ╬╢╓°╚╬╥╗╖ذ╥µ╩╟╖ً▒╗╟╓║خاoمP╛o╥ز��ةث╚ق╣√│╨╒J▀@ء╙╡─╖ذ╥µ╜YءïمP╧╡���ثش╦∙╓^ة░نp╓╪╖ذ╥µ╒ôة▒╛═╩د╚ح┴╦╫≈╙├┐╒لg���ةث
┴و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ثش┤╬╥ز╖ذ╥µ┐╔─▄▒╗╓≈╥ز╖ذ╥µ╞┴▒╬ةث╘┌نp╓╪╖ذ╥µ╒f╡─╒ô╫C▀ë▌ï╓╨�ثش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âHâH╩╟▒وî╙╖ذ╥µثش╢°╣س▒è╜ة┐╡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t╩╟╡╫î╙╖ذ╥µةثôQ╤╘╓«�ثش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╛S│╓ثشأw╕∙╡╜╡╫╩╟ئل┴╦▒ث╫o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ثشâ╔╒▀▒╗╢ذ╬╗ئل╥╗╖N╝â┤ظ╡─╩╓╢╬┼c─┐╡─مP╧╡�����ةث▀@ء╙╥╗و�����ثش╘┌âHâH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س▓ت╬┤îخ╣س▒è╜ة┐╡��ةت╔·├ⁿ╘ه│╔î┘|ôp║خ╡─êِ║╧�����ثش─┐╡─╛▀╙╨îخ╩╓╢╬╡─╜^îخâئ(yذصu)╘╜╨╘ثش╣ج╛▀└و╨╘▒╗═م╚س╧√فَ╘┌─┐╡─└و╨╘╡─مP╒╒╓«╓╨��ةث▀@╖N╒ô╫C▀ë▌ï╘┌╒√ٍw╔╧║ِ┬╘┴╦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╫╘╘┌╡─╒²«¤╗»âr╓╡�ثش┐╔─▄╩╣╞غ╫â╡├├√┤µî═ِةث
╘┌╕┼─ى╒J╢ذ╔╧╕╜î┘╙┌╟░╓├╖ذ���ثش╢°╟░╓├╖ذ╕┼─ى▒╛╔و┤µ╘┌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╓«╗ه═ش╡─▒│╛░╧┬��ثشة░نp╓╪╖ذ╥µ╒ôة▒╚╘╛▀╙╨╥╗╢ذ╡─شFî║╧└و╨╘����ةث╡س╩╟���ثش▀@╖N╖╜░╕îتâ╔╖N╖ذ╥µ╥ـئل▒╦┤╦ؤ_═╗╡─مP╧╡ثش▀M╢°╙ك╥╘╧ض╗حآض║ظ┼c╧▐╓╞����ثش┐╔─▄╩╣â╔╖N╖ذ╥µلg╡─²Réغ╨╘╜Yءï▒╗╒`╒Jث╗▓╗âH╚ق┤╦�ثش╦ⁿ▀┐╔─▄╩╣┤╬╥ز╖ذ╥µ╠╙┌╓≈╥ز╖ذ╥µ╡─م╙░╓«╧┬ثش╔ُ╓┴╪╡╫╤═ؤ]╘┌îخ╓≈╥ز╖ذ╥µ╡─مP╟╨╓«╓╨�����ةث╥ٌ┤╦ثش▀@╖N╖ذ╥µلgمP╧╡╡─╓╪╨┬مUطî�ثشâHâH╩╟╥╗╖Nآض╥╦╩╜╡─╕─┴╝ثش╩╟╥╗╖N╘┌╜╙╩▄╟░╓├╖ذ╦∙╘O╢ذ╡─نp╓╪╖ذ╥µ╟░╠ط╧┬╡─╛╓▓┐âئ(yذصu)╗»�ثشاo╖ذ╘┌╕∙▒╛╔╧╧√فَâ╔╖N╖ذ╥µ╓«لg┐╔─▄╡─╛oêمP╧╡ةث
3.╖ذ╥µâنx╡─çL╘ç┼c▀z║╢
┴ى╚╦╨└╧▓╡─╩╟���ثش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╨▐╙╒▀éâ╥╤╥ظ╫R╡╜╔╧╩ِ╡─╖ذ╥µ╗ه═شûى}�ثش▓تîخ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▀M╨╨┴╦╜Yءï╨╘╒{╒√�ةث▀@╖N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╒{╒√����ثش▒M╣▄▓ت▓╗╛▀╙╨è╓╞╨╘╡─╥(guذر)╖╢╨د┴خثش╡سîنH╔╧ـ■╩╣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�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╧ضّز╩╒┐s���ةثîخ╙┌╘صة░░┤╝┘╦╒ôة▒ة░░┤┴╙╦╒ôة▒╓╨╬╝â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╨ئل���ثششF╘┌─╝┘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╖╢«ب╓╨▒╗┼┼│²│ِ╚ح���ثش▓ت▓┐╖╓▒╗╓├╚نشF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╓«╓╨╝╙╥╘╥(guذر)╓╞ةث╧ضّز╡╪����ثش╙╔╙┌▀@╨ر╨╨ئلاo╖ذ╘┘▒╗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╦∙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�ثش╨╠╖ذ▒╪وأ├µ╧ٌشF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╡┌124ùl╘O╓├╨┬╡─▒ث╒╧╨╘╥(guذر)╖╢ةث▀@╛═╩╟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╓╨╘ِ╘O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╕∙▒╛╨╘╙آC���ةث═ذ▀^╘ِ╘O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ثشîخ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╓╨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╩ر╝╙╨╠╩┬╓╞▓├�����ثش╝╚┐╔┼c╟░╓├╖ذ╡─╨▐╒²╨╬│╔▀b╧ض║َّز╓«▌�����ثش╥▓┐╔╥╘ؤ╤a╥ٌ╟░╓├╖ذ╓«╨▐╒²╢°îد╓┬╡─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╥(guذر)╓╞░ن╜▓╗╫ع╡─ûى}�����ةث
▀@ء╙╥╗و�����ثششF╨╨ة╢╨╠╖ذة╖╓╨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╥(guذر)╖╢ٍw╧╡���ثش▒ع╙╔╡┌141ùl��ةت╡┌142ùl╝░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╦∙╜M│╔�����ةث─ّز╚╗╜╟╢╚╦╝┐╝�����ثش▀@╚²é╫ي├√╘┌╖ذ╥µ▒ث╫o╚╬╒╔╧ّز╨╬│╔▌^╟ف╬·╡─╖╓╣جث║╡┌141ùl┼c╡┌142ùl╥╘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ئل▒ث╫o╖ذ╥µ��ثش╢°╡┌142ùl╓«╥╗t╥╘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╛S│╓ئل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���ةث╡┌141ùl�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îخ╣س▒è╜ة┐╡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╡─▒ث╫o����ثش╩╟╥╘╧ضمP╦╞╖ء╦£╩ئل╜ل┘|ثشâ╔╒▀╘┌î┘|╔╧┐╔╜y║╧ئلة░▀`╖┤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╖╕╫ية▒�ةثâ╔╒▀╡─à^(qذ▒)eâH╘┌╙┌ثش╝┘╦╕ⁿئل╫ت╓╪╦╞╖│╔╖▌ء╦£╩╡─╝s╩°╥ظ┴x���ثش╢°┴╙╦t╥╘│╔╖▌ء╦£╩╓«═ظ╡─╞غ╦√╦╞╖ء╦£╩ئل║ظ┴┐╗∙£╩����ةث═شـr��ثش─╖ذ╥µ╟╓║خ╡─مP┬ô╨╘┘|╔╧┐┤��ثش╡┌141ùl╓╗╨كîخ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╨╬│╔│ل╧ٍ╬ثنU╝┤┐╔ثش╡┌142ùlt╨ك╥زîخ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╘ه│╔î║خ╜Y╣√╖╜─▄│╔┴ت�����ةث╢°╨┬╘ِ╡─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�ثشt▓ت▓╗╥╘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ئل╓▒╜╙▒ث╫o─┐╡─��ثش╥▓▓╗╥╘╧ضمP╦╞╖ء╦£╩ئل║ظ┴┐╓╕طء�����ةث▀@╥╗╫ي├√╓╝╘┌îخ╥╗░ع╡─ç°╝╥╦╞╖▒O(jiذةn)╣▄╓╚╨ٌ╝╙╥╘╛S│╓���ثش▓تîخ▀`╖┤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╔·«a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╨╨ئل╓«═ظ╡─╞غ╦√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╝╙╥╘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ةث╥ٌ┤╦���ثش╘ô╨┬╘ِ╫ي├√▒╗╖Qئلة░╖┴╡K╦╞╖╣▄└و╫ية▒��ةث╚ق┤╦╥╗و���ثش╥╗╖N╦╞╖╖╕╫يىI╙ٌ╡─نp▄ë╥(guذر)╓╞ٍw╧╡▒ع║َ╓«╙√│ِةث
╡سûى}╩╟���ثش╨┬╘ِ╓«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����ثش▓تؤ]╙╨═م╚س╫ً╒╒╔╧╩ِ╖ذ╥µ╖╓┴ت╡─▀ë▌ï��ةث╘┌╘ôùl╓╨�ثش│²╥(guذر)╢ذ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╥ز╟ٍ═ظثش▀îت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╫≈ئل▒╛╫ي╡─│╔┴تùl╝■��ةث┤╦╖N╘O╓├╡─┐╔─▄└و╙╔╘┌╙┌ث║▒╪وأà^(qذ▒)╖╓╫≈ئل╨╨╒■▀`╖ذ╡─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┼c╫≈ئل╨╠╩┬▓╗╖ذ╡─╖┴╡K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╖╕╫ي�ثش▓ت┼c╫≈ئل╟░╓├╖ذ╡─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▀m«¤└صل_╛ضنxةث╥ٌ┤╦�ثش┐╔═ذ▀^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╡─لTآّ╘O╓├ثش▀M╥╗▓╜╠ط╔²▓╗╖ذ│╠╢╚�����ثش▓تءï╓■╨╠╩┬▓╗╖ذ╡─زأ┴تîٍwâ╚║ص�ةث╡س╚ق┤╦╥╗وثش▌▒╪«a╔·╚ق╧┬ûى}�ةث
╩╫╧╚ثش┐╔─▄╩╣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┴ت╖ذ╕─▀M│╔╣√╩╚╗اo┤µ����ةث┘|╤╘╓«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╪╨┬╜ق╢ذ┴╦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ثش▓تîت╘صوة░░┤╝┘╦╒ôة▒ة░░┤┴╙╦╒ôة▒╡─╟ل╨╬│لنx│ِو╢°╓├╚ن╡┌124ùl╓«╓╨�����ثش▀@╛∙╩╟╥╘╔·├ⁿ╜ة┐╡╖ذ╥µ┼c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╖ذ╥µ╡─▀m«¤╖╓نxئل╖╜╧ٌ╡─�ةث╔╧╩ِ╫ِ╖ذ┼c▀@╥╗╖╜╧ٌ▒│╡└╢°ًYثش▓╗âH╩╣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╖ذ╥µ╖╓نx┼c╝â╗»╨د╣√اo╖ذ╘┌▒ث╒╧╖ذ╔╧╡├╥╘îشF�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ـ■╩╣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┼c╨╠╖ذ╡─╖ذ╥µ╘O╓├▀ë▌ï╘┘┤╬╡╓مُ�����ةث
╞غ┤╬ثش┐╔─▄╩╣╦╛╖ذ▓┘╫≈╓╨╡─╒J╢ذنy╢╚ي@╓°╠ط╔²�ةث╚ق╟░╦∙╩ِثش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îت╘ص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╙ك╥╘╨▐╕─����ثش▓ت╚ة╧√┴╦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▀@╥╗╥ز╟ٍةث╓«╦∙╥╘╫≈│ِ╔╧╩ِ╨▐╙�����ثش╒²╩╟╥ٌئل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ة▒▀@╥╗╧▐╢ذ╜o╦╛╖ذî█`دو┴╦╛▐┤ٍ└د¤_��ة���ثة░â╔╕▀ة▒╧╚║ٍ╙┌2001─م����ةت2009─م░l(fذة)▓╝┴╦ة╢╖ذطîة▓2001ة│10╠ûة╖ة╢╖ذطîة▓2009ة│9╠ûة╖â╔é╦╛╖ذ╜ظطî�����ثش▓ت╝»╓╨îخ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ة▒╡─└و╜ظ║═▀m╙├╙ك╥╘╘¤╝أ╥(guذر)╢ذ�ةث╢°╘┌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░╦ثرة╖│ِ┼_╓«║ٍ��ثش▓╗âHي@╓°╜╡╡═┴╦╒J╫ي╡─î┘|لTآّ�ثش╢°╟╥╩╣╫╖╘VآCمP╡─╫C├≈╪ôô·ءO┤ٍ£p▌p�����ة�����ث┐╔╥╘╧ن╥è����ثش╚ق╣√└^└m(xذ┤)▒ث┴َ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▀@╥╗╥ز╟ٍ�����ثشاo╥╔îت╘ِ╝╙îٍw┼c│╠╨ٌ╔╧╡─╒J╢ذ└دنy�ثش╥▓îتءO┤ٍ╡╪║─╔ت╦╛╖ذآCمP╡─╜ظطî┘Y╘┤ةث
░┤╒╒╨┬╘ِ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╘O╢ذ����ثش▓╗âH╨ك╥ز┼╨¤ض╨╨ئل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╠╪╒≈ثش╢°╟╥╨ك╥ز┼╨¤ض╨╨ئل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╛▀╙╨╛▀ٍw╡─�ةتç└╓╪╡─╬ثنU���ثش╕ⁿ╓╪╥ز╡─╩╟ثش╨ك╥ز╘┌â╔╒▀╓«لg╜ذ┴تâ╚╘┌مP┬ô╨╘�����ةثّز«¤│╨╒J�����ثش▒M╣▄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╨ئل┐╔─▄╠N║ش╓°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│ل╧ٍيLنU�ثش╡س╘┌┤╦╖N│ل╧ٍ╬ثنU╔╨╬┤شFî╗»╓«╟░ثش╥ز╓▒╜╙╒J╢ذ╨╨ئل╘ه│╔┴╦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╛▀ٍw╬ثنU╩╟▌^ئل└دنy╡─���ةث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╨ئل«¤╚╗╛▀╙╨╖ذ╥µ╟╓║خ╨╘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▀@╖N╟╓║خ╨╘╩╟╓▒╜╙╓╕╧ٌ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▒╛╔و╡─��ةث╝┤▒ع╒Jئل�ثش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╛S╫o╥╘îخ╚╦ٍw╜ة┐╡�ةت╔·├ⁿ╡─▒ث╫oئل╞غ╜KءO─┐ء╦ثش╙╔┤╦����ثش╞╞ë─╫كôُî╙╖ذ╥µ╡─╨╨ئلîخ╙┌╡╫î╙╖ذ╥µ╥▓╛▀╙╨─│╖N│ل╧ٍ╬ثنU╨╘����ثش╡س╩╟���ثش▀@╖N│ل╧ٍ╡─╬ثنU╨╘ؤQ▓╗─▄╓▒╜╙╠°▄S╡╜╛▀ٍw╡─╬ثنU╨╘��ةثôQ╤╘╓«ثش▓╗─▄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╡─╠╪╒≈����ثش╓▒╜╙═م│╔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╛▀ٍw╬ثنU╡─╒J╢ذةث▀@└ي▓╗âHمP╔µ╖ذ╥µى╨═╡─╙╬╥╞���ثش╢°╟╥╔µ╝░╟╓║خ╨╬╩╜╡─▐DôQ���ثش▓ت╟╥â╔╒▀╩╟╘┌╥╗┤╬┼╨¤ض╓╨═شـr═م│╔╡─ةث╢°╩┬î╔╧����ثش┤╦╖NمP┬ô╨╘╡─°آ£╧ثش╨ك╥ز═ذ▀^إu┤╬╒╣ل_╡─╦╝┐╝┼╨¤ضو╙ك╥╘╠ى╤a��ةث╥ض╝┤ثش╠╪╢ذ╦╞╖╣▄└و╥(guذر)╖╢╦∙▒ث╫o╡─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╛▀ٍw╩╟╩▓├┤�ث┐▀@╖N╛▀ٍw╡─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┼c╣س▒è╜ة┐╡╖ذ╥µ╓«لg╩╟║╬╖NمP╧╡ث┐┤²ؤQé░╕╓╨╡─╨╨ئل╩╟╖ً▀`╖┤┴╦╘ô╥(guذر)╖╢�����ثش▓تîخ╘ô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╘ه│╔┴╦î┘|╟╓║خ����ث┐▀@╖Nîخ╓╚╨ٌ╨╘╖ذ╥µ╡─î┘|╟╓║خثشîخ╙┌╣س▒è╜ة┐╡╖ذ╥µ╘ه│╔┴╦║╬╖N╨╘┘|╡─═■├{�ث┐╜Y║╧┤²ؤQé░╕╡─╟ل╣إ(jiذخ)┼╨¤ضثش╞غîخ╣س▒è╜ة┐╡╡─═■├{╩╟╖ً╥╤╜ؤشFî╗»�����ةت┐═╙^╗»║═╛▀ٍw╗»����ث┐▓╗نy░l(fذة)شFثش╙╔╙┌╘ِ╝╙┴╦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╡─╧▐╓╞�ثش╩╣▒╛╫ي▓╗âH╘┌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ى╨═╔╧│╩شF│ِ═║╧ء╙ّB(tذجi)ثش╢°╟╥╘┌▓╗═ش╖ذ╥µى╨═╡─╟╓║خء╙ّB(tذجi)╔╧╛▀╙╨▓╗═ش╥ز╟ٍ���ةث╚ق║╬╘┌طءîخ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î║خ┼cطءîخ╣س▒è╜ة┐╡╡─╛▀ٍw═■├{╓«لg�����ثش╝▄ءï╞غâ╚╘┌╡─╩┬î┼c▀ë▌ïمP┬ô�����ثشîتîخ╦╛╖ذî█`╡─╛▀ٍw╒J╢ذ╠ط│ِç└╛■╠َّ≡(zhذجn)�����ةث
╫ى║ٍ����ثش╛╓▓┐ٍw╧╡╡─àf╒{╨╘┤µ╘┌╚▒║╢�����ةثîنH╔╧��ثش╝┤╩╣îت▒╛╫ي╫≈ئل╝â╒²╨╨╒■╖╕و╘O╓├��ثش╥▓▓ت▓╗╥╗╢ذ╨ك╥ز═ذ▀^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▀@╥╗╧▐╓╞و└صل_┼c╬╝â╨╨╒■▀`╖ذ╨╨ئل╓«لg╡─╛ضنx����ةث╡─┤_���ثش╨╠╩┬▀`╖ذ╨╘╧ضîخ╙┌╨╨╒■▀`╖ذ╨╘ّز╙╨╞غ╧ضîخزأ┴ت╨╘ثش╡س┤╦╖Nزأ┴ت╨╘═م╚س┐╔╥╘═ذ▀^▓╗╖ذ│╠╢╚╡─╠ط╔²�����ثش╢°▓╗╥╗╢ذ╨ك╥ز═ذ▀^┤_┴ت▓╗═ش╙┌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╡─▒ث╫o╖ذ╥µى╨═╢°س@╡├���ةثمP╙┌┤╦ⁿc�����ثش┴_┐╦╨┴╘°╕╗╙╨╜╠╥µ╡╪╓╕│ِ�ثشة░╨╠╩┬╖╕╫ي║═╓╚╨ٌ▀`╖┤╓«لg▓╗┐╔─▄═ذ▀^╥╗é╖ذ╥µ╟╓║خ╡─╙╨اoو╝╙╥╘à^(qذ▒)╖╓���ثش╥ٌئلâ╔╒▀╢╝îخ╖ذ╥µ╘ه│╔╟╓║خ�ةثâ╔╒▀لgà^(qذ▒)╖╓╡─â╚╘┌ء╦£╩╘┌╙┌▌o╓·╨╘╘صt�����ثش╝┤«¤╚╦éâîخ╙┌▀`╖ذ╨╨ئل┐╔╥╘╙├╕ⁿئل▌p╛╡─╓╞▓├╩╓╢╬╝╙╥╘ّ═╠��ةتàs─▄ëٌ╚ة╡├╡╚═ش╗ٌ╕ⁿ║├╡─╨د╣√ـrثش─╟├┤╛═╖┼ùë╨╠┴P╡─î╩ر����ةث╦∙╥╘«¤îخ─│╥╗▀`╖ذ╨╨ئلâH╥(guذر)╢ذ╓╚╨ٌ▀`╖┤╡─╖ذ┬╔║ٍ╣√ـrثش▓ت▓╗╩╟╒f┤╦╠╚▒╖خ╦∙▒ث╫o╡─╖ذ╥µ���ةث╥ٌ┤╦����ثش╨╠╩┬╖╕╫ي┼c╓╚╨ٌ▀`╖┤╓«لg╡─à^(qذ▒)e╓≈╥ز╩╟┴┐╔╧╢°╖╟┘|╔╧╡─ة▒���ةث
╘┌╨┬╘ِ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╓╨�ثش╖ذ╢ذ╨╠▒╗╘O╓├│╔â╔آnث║3─م╥╘╧┬╙╨╞┌═╜╨╠����ث╗3─م╥╘╔╧7─م╥╘╧┬╙╨╞┌═╜╨╠ةث╞غ╓╨����ثش╟░╥╗╨╠آn╩╟╥╘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ئللTآّ�����ث╗║ٍ╥╗╨╠آnt╥╘ة░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╘ه│╔ç└╓╪╬ث║خ╗ٌ╒▀╙╨╞غ╦√ç└╓╪╟ل╣إ(jiذخ)╡─ة▒ئلùl╝■ةث╒\╚ق╔╧╩ِ�ثشة░╞غ╦√ç└╓╪╟ل╣إ(jiذخ)ة▒╡─╘O╓├îنH╔╧┐╔╥╘░l(fذة)ô]▓╗╖ذ│╠╢╚╠ط╔²╡─╫≈╙├ثش▓ت╙╔┤╦┤_┴ت╥╘▌o╓·╨╘╡─╖ذ╥µ▒ث╫oئل╣خ─▄╓╕╧ٌ╡─�����ةتزأ┴ت╡─╨╠╩┬▓╗╖ذâ╚║ص��ةث╡س▀z║╢╡─╩╟�ثش┴ت╖ذ╒▀╝╚ؤ]╙╨îت╞غ╫≈ئل╚ن╫يلTآّ╢°╘O╓├ثش╥▓ؤ]╙╨îت┤╦╖N│╠╢╚╨╘ء╦£╩╥╗╥╘╪ئ╓«╡╪▀m╙├╡╜╦∙╙╨╨╠آn���ةث╙╔┤╦«a╔·╡─▀ë▌ï¤ض┴╤╩╟ث║╫≈ئل╥╗╖N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╖╕╫ي���ثش┐╔╥ٌ┴و╥╗╖N╖ذ╥µةزةز╣س▒è╜ة┐╡╡─╛▀ٍw╬ثنU╗ٌî║خ╜Y╣√╢°╙░وّ▒╛╫ي╡─│╔┴ت╝░╞غ╨╠╪ا╕▀╡═ث╗╢°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▒╛╔و╡─▀`╖┤╗ٌ╟╓║خ│╠╢╚����ثشàs▓╗─▄╙░وّ▒╛╫ي╡─│╔┴تثش╢°╓╗─▄╙░وّ╨╠╪ا╕▀╡═�����ةث
ثذ╚²ثر┐╔─▄╡─╠┴P┬ر╢┤
╒\╚ق╔╧╩ِ�����ثش╨╠╖ذ╔╧╝┘┴╙╦╡─╒J╢ذ╩┬î╔╧اo╖ذ┼c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├ôع^ةث▀@ء╙╥╗و�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╨îخ╙┌╝┘╦ةت┴╙╦╡─╜ق╢ذء╦£╩╡─╒{╒√ثذ╡┌98ùlثر�����ثش╥╘╝░îت▓┐╖╓╘ص╧╚╡─¤M╓╞╨═╝┘╦╗ٌ¤M╓╞╨═┴╙╦�ثش┼▓╚ن╬╝â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╙ك╥╘╥(guذر)╓╞ثذ╡┌124ùlةت╡┌125ùlثر╡─╫ِ╖ذ����ثش▌▒╪▀Bد╨╘╡╪╙░وّ╨╠╖ذ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ةث▀@╓≈╥زٍwشF╘┌ث║─│╖N╟ل╨╬╘صو╘┌¤M╓╞╨═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â╚�ثششF╘┌▒╗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┼┼│²╘┌╝┘╦ةت┴╙╦╖╢ç·╓«═ظ��ثش╚ق╣√▀M╚ن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���ةت╡┌125ùl╓«╓╨ثش═شـr▒╗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╦∙╬ⁿ╝{����ثشt╚╘╚╗═شـr╩▄╡╜╨╨╒■┴P┼c╨╠╩┬┴P╡─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ث╗╚ق╣√╓╗╩╟▀M╚ن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ةت╡┌125ùl╓«╓╨���ثش╡س╬┤▒╗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╦∙╬ⁿ╝{�ثشtâHءï│╔╨╨╒■▓╗╖ذ��ثش▓╗╩▄╨╠┴P╠┴P��ث╗╚ق╣√╝╚╬┤▀M╚ن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24ùl�ةت╡┌125ùl╓«╓╨ثش╙╓╬┤▒╗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╦∙╬ⁿ╝{�ثشt╝╚▓╗ءï│╔╨╨╒■▓╗╖ذثش╥▓▓╗╩▄╨╠┴P╠┴P�����ةث▀@╖N╒{╒√╖╢ç·╡─╫â╗»�ثش┐╔═ذ▀^╚ق╧┬┬╖╜╝╙╥╘آz╥ـةث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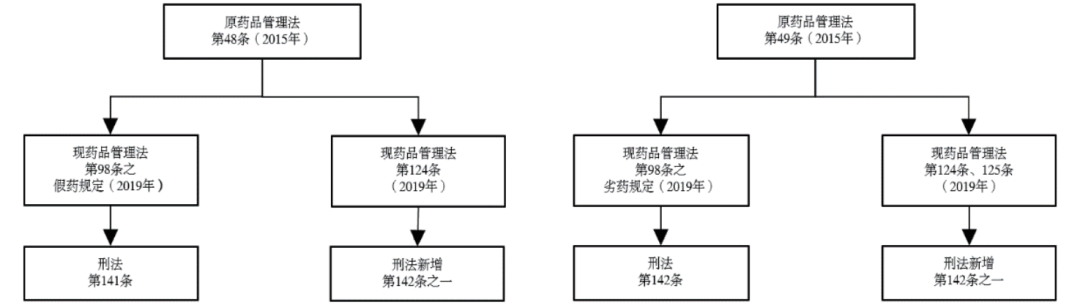
êD1ةة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╥(guذر)╓╞├}╜j
╕∙ô■╔╧╩ِ╥(guذر)╖╢├}╜j�ثش╬╥éâ┐╔╥╘îخ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ةت╡┌49ùl╓«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��ثش╩╟╖ً╚╘╠╙┌╨╠╖ذ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╙ك╥╘╥╗╥╗آz╥ـ�����ةثآz╥ـ╡─╜Y╣√╩╟���ثش╙╨╚²╖N╟ل╨╬┤µ╘┌▌^ئلن[├╪╡─╫â╗»����ةث╦ⁿéâ╘صî┘╙┌╨╠╖ذ╥(guذر)╓╞╡─╖╢ç·��ثش╡س╙╔╙┌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╨▐╙�����ثش╥▌│ِ┴╦╨╠╖ذ╠┴P╖╢ç·╓«═ظ��ةث▀@╚²╖N╟ل╨╬╝┤╩╟ث║ثذ1ثر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░┤╝┘╦╒ô╓╨╡─ة░╩╣╙├╥└╒╒▒╛╖ذ▒╪وأ╚ة╡├┼·£╩╬─╠û╢°╬┤╚ة╡├┼·£╩╬─╠û╡─╘ص┴╧╦╔·«a╡─ة▒�����ث╗ثذ2ثر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9ùl░┤┴╙╦╒ô╓╨╡─ة░╓▒╜╙╜╙╙|╦╞╖╡─░ⁿ╤b▓─┴╧║═╚▌╞≈╬┤╜ؤ┼·£╩╡─ة▒ث╗ثذ3ثر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░┤╝┘╦╒ô╓╨╡─ة░╥└╒╒▒╛╖ذ▒╪وأآzٌئ╢°╬┤╜ؤآzٌئ╝┤غN╩█╡─ة▒����ةث
╘┌2015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╓╨����ثشة░╩╣╙├╥└╒╒▒╛╖ذ▒╪وأ╚ة╡├┼·£╩╬─╠û╢°╬┤╚ة╡├┼·£╩╬─╠û╡─╘ص┴╧╦╔·«a╡─ة▒ثش░┤╝┘╦╒ô���ةث═ش╖ذ╡┌49ùlt╥(guذر)╢ذ�ثشة░╓▒╜╙╜╙╙|╦╞╖╡─░ⁿ╤b▓─┴╧║═╚▌╞≈╬┤╜ؤ┼·£╩╡─ة▒��ثش░┤┴╙╦╒ô�ةث╚╗╢°ثش╘┌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��ثش┴ت╖ذ╒▀╘┌îخ╝┘╦║═┴╙╦╙ك╥╘╜ق╢ذ╓«║ٍ�ثش╙╓╬زأ╥(guذر)╢ذ┴╦ة░╜√╓╣╩╣╙├╬┤░┤╒╒╥(guذر)╢ذî╘uةتî┼·╡─╘ص┴╧╦���ةت░ⁿ╤b▓─┴╧║═╚▌╞≈╔·«a╦╞╖ة▒��ةث▀@ي@╚╗╩╟îت╔╧╩ِ╟ل╨╬┼c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├≈┤_à^(qذ▒)╖╓ثش▓تîت╞غ┼▓│ِ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╖╢«ب�ةث«¤╚╗ثش┼▓│ِ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╖╢«ب����ثش▓ت▓╗╥ظ╬╢╓°╖┼ùë╨╨╒■╥(guذر)╓╞ةث┼▓│ِ╓«║ٍ��ثش╘ô╖ذ╡┌124ùl╡┌3┐ى╓╨├≈┤_╠┴Pة░╩╣╙├╬┤╜ؤî╘u��ةتî┼·╡─╘ص┴╧╦╔·«a╦╞╖ة▒�ثش╢°îخ╙┌ة░╩╣╙├╬┤╜ؤî╘uةتî┼·╡─░ⁿ╤b▓─┴╧║═╚▌╞≈╔·«a╦╞╖ة▒╡─╟ل╨╬�ثشt╘┌╡┌125ùl╓╨╝╙╥╘╠┴Pةث╡س╓╡╡├╫ت╥ظ╡─╩╟�ثش╘┌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╨┬╘ِ╡─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╓╨ثش╔╧╩ِâ╔╖N╟ل╨╬╛∙╬┤▒╗╝{╚ن���ة����ث┐╔╥èثش╗∙╙┌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╨▐╙��ثش╔╧╩ِâ╔╖N╟ل╨╬─╨╨╒■╖ذ╡─╝┘╦�ةت┴╙╦╖╢«ب╓╨▒╗┼┼│²│ِ╚ح��ثش╡س╚╘╚╗╫≈ئل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╨╨╒■▀`╖ذ╨╨ئل╝╙╥╘╠┴P����ةث▀@╥╗╫â╕ⁿ└^╢°╥²░l(fذة)╨╠╩┬╠┴P╖╢ç·╡─╫â╗»ثش╞غ▓╗╘┘▒╗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ثذ╔·«a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ثر�ةت╡┌142ùlثذ╔·«a��ةتغN╩█┴╙╦╫يثر╦∙╥(guذر)╓╞��ثش╥▓╬┤▒╗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ثذ╖┴║خ╦╞╖╣▄└و╫يثر╦∙║ص¤z���ثش╙╔┤╦├ô╥▌│ِ╨╠┴P╠┴P╡─╔غ│╠����ةث
╢°îخ╙┌ة░╥└╒╒▒╛╖ذ▒╪وأآzٌئ╢°╬┤╜ؤآzٌئ╝┤غN╩█╡─ة▒╡─╟ل╨╬ثش╘ص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48ùl╥(guذر)╢ذ░┤╝┘╦╒ô���ثش╞غ╥▓╛═▀M╚ن┴╦ة╢╨╠╖ذة╖╘ص╡┌141ùl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����ةث╡س╘┌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8ùl╓╨���ثش▀@╖N╟ل╨╬▒╗┼┼│²│ِ╝┘╦┼c┴╙╦╡─╖╢ç·╓«═ظ�����ثش┬غ╚ن╘ô╖ذ╡┌124ùl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╓«╓╨�����ةث╧ضّز╡╪�ثش╦ⁿاo╖ذ╘┘╙╔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╦∙╒{╒√���ثش╓╗─▄▐D╢°┐╝ّ]╩╟╖ً┬غ╚ن╨┬╘ِ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╠┴P╖╢ç·����ةث╘┌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╡─╥╗î╕ف╓╨ثش▀@╖N╟ل╨╬▒╗╝{╚ن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╡┌3┐ى╓«╓╨��ثش╡س╘┌╞غ║ٍ╡─╢■î╕ف╓╨▒╗h│²�ثش╘┌╫ى║ٍ═ذ▀^╡─╚²î╕ف╓╨╥▓╘┘╬┤│ِشFةث«¤╚╗��ثش╘┌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╡─╡┌4┐ى╓╨�ثش╥(guذر)╢ذ┴╦ة░╛╘ه╔·«aةتآzٌئ╙ؤغؤ╡─ة▒╟ل╨╬�ةث╡سûى}╩╟ثشة░▒╪وأآzٌئ╢°╬┤╜ؤآzٌئة▒┼cة░╛╘هآzٌئ╙ؤغؤة▒╘┌╨╨ئلء╙ّB(tذجi)╔╧▓ت▓╗═م╚س╥╗╓┬����ثشîخ▒╪وأآzٌئ╢°╬┤╜ؤآzٌئ╡س▓ت╬┤╛╘هآzٌئ╙ؤغؤ╡─╨╨ئل��ثش╘صو┐╔░┤╒╒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╠┴P����ثش╡سشF╘┌╝╚اo╖ذ▒╗╡┌141ùl╠┴Pثش╥▓نy╥╘▒╗╝{╚ن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╓«╓╨�ةث
«¤╚╗ثش╔╧╩ِ╚²╖N╟ل╨╬╡─│²╫ي╗»��ثش╥ض┐╔─▄╩╟┴ت╖ذ╒▀╙╨╥ظئل╓«��ثش╢°╖╟▀`╖┤╙ïإ╡─╠┴P┬ر╢┤ةث╡س─î┘|╜╟╢╚┐╝▓ه�����ثش╚²╖N╨╨ئل╢╝╙╨╨╠╩┬╠┴P╓«▒╪╥ز�����ةث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��ثش╦ⁿéâ╢╝ç└╓╪▀`╖┤┴╦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�ث╗┴و╥╗╖╜├µثش╦ⁿéâ╙╓╢╝îخ╣س▒è╡─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«a╔·┴╦═■├{����ةث╦╞╖╘ص▓─┴╧╓«╦∙╥╘▒╪وأ╜ؤ▀^┼·£╩ثش╩╟╥ٌئل╘ص▓─┴╧╩╟╦╞╖╡─â╚╘┌ءï│╔▓┐╖╓�ثش╞غ░▓╚س┼c┘|┴┐╓▒╜╙مP║ُ╗╝╒▀╡─╔وٍw╜ة┐╡ةث╢°╦╞╖╡─░ⁿ╤b▓─┴╧┼c╚▌╞≈نm╖╟╦╞╖╡─â╚╘┌ءï│╔▓┐╖╓����ثش╡س╚ق╣√╞غ┼c╦╞╖╓▒╜╙╜╙╙|�ثش╥╗╡ر┤µ╘┌░▓╚س┼c┘|┴┐ن[╗╝��ثش╥▓═شء╙┐╔─▄îخ╗╝╒▀╜ة┐╡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╘ه│╔═■├{����ةث┤╦═ظثش╦╞╖آzٌئ╛▀╙╨┤_▒ث╦╞╖╖√║╧ç°╝╥ء╦£╩╡─î▓ل╣خ─▄�ةث╦╞╖╔·«a╞ٍءI(yذذ)ّز«¤îخ╦╞╖▀M╨╨┘|┴┐آzٌئثش▓╗╖√║╧ç°╝╥╦╞╖ء╦£╩╡─��ثش▓╗╡├│ِS��ةث╥╗╡ر▀`╖┤┤╦╖N╥(guذر)╢ذ�ثش╥▓═شء╙╛▀╙╨╬ث║خ╣س▒è╓«╜ة┐╡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╡─│ل╧ٍ═■├{ةث▒M╣▄▀@╨ر╟ل╨╬▓╗─▄╓▒╜╙░┤╝┘╦╗ٌ┴╙╦╝╙╥╘╒J╢ذ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╙╔╙┌╦ⁿéâ╛▀╙╨ç└╓╪▀`╖┤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╡─╠╪╒≈ثش▓ت╛▀╙╨îخ▓╗╠╪╢ذ╣س▒è╜ة┐╡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╡─│ل╧ٍ╬ثنUثش╥ٌ╢°╚╘╛▀╙╨î┘|╡─╠┴P▒╪╥ز╨╘��ثش╙╨▒╪╥ز╝{╚ن╨┬╘ِ╡─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╝╙╥╘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��ةث
╚²�ةت╨╨ئل╖╜╩╜╡─═╪╒╣ث║
ة░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ةت┴╙╦���ثش
╢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ة▒
ثذ╥╗ثر╨╨ئل╖╜╩╜╡─═╪╒╣╝░╞غ▓╗╫ع
╩┬î╔╧�ثش╘┌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│ِ┼_╓«╟░�����ثشئل┴╦╗╪ّزî█`╓╨╡─╓╬└و╨ك╥ز��ثشة░â╔╕▀ة▒╙┌2014─م═ذ▀^┴╦ة╢مP╙┌▐k└و╬ث║خ╦╞╖░▓╚س╨╠╩┬░╕╝■▀m╙├╖ذ┬╔╚َ╕╔ûى}╡─╜ظطîة╖�ثشîخ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┼c╡┌142ùl╓╨╡─ة░╔·«aة▒║═ة░غN╩█ة▒╨╨ئل╙ك╥╘┴╦¤Uê╨╘╜ظطîثش═شـr│غ╖╓┐╝ّ]┴╦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╡─░ل╔·╨╘╨╨ئلثش▓ت▒M┴┐╝{╚ن╞غ╣▓═ش╖╕╫يâ╚╝╙╥╘╠┴P�����ةث┤╦═ظ��ثشة░â╔╕▀ة▒╙╓╙┌2017─م═ذ▀^┴╦ة╢مP╙┌▐k└و╦╞╖�ةتطt(yذر)»ا╞≈╨╡╫تâ╘╔م╒ê▓─┴╧╘ه╝┘╨╠╩┬░╕╝■▀m╙├╖ذ┬╔╚َ╕╔ûى}╡─╜ظطîة╖ثش▓تîخ╦╞╖���ةتطt(yذر)»ا╞≈╨╡╫تâ╘╔م╒ê▓─┴╧╘ه╝┘╨╨ئل╡─╫ي├√▀m╙├ûى}╙ك╥╘┴╦مUطî����ةث
▀@╨ر╦╛╖ذ╜ظطî╡─│ِ┼_�����ثشاo╥╔╩╟╗∙╙┌شFî╡─╦╞╖╖╕╫ي╓╬└و╨ك╥ز���ثش▓╗╡├▓╗╘┌âH╙╨╡─ة░╔·«aة▒ة░غN╩█ة▒╨╨ئل╓«â╚╝╙╥╘¤Uêثش┐╔╓^ة░┬▌╬çأج└ي╫ِ╡└êِة▒��ةث╞غ╘┌╫ى┤ٍ╖╢ç·╡╪¤Uê╨╠╖ذ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╓«╙ضثش╥ضيû╩▄═╗╞╞╬─┴x╔غ│╠�ةت╞╞ë─╫ي╨╠╖ذ╢ذ╓≈┴x╓«╓╕╪اةث└²╚ق��ثش║╧│╔���ةت╛س╓╞��ةت╠ط╚ة��ةتâخ┤µ��ةت╝╙╣ج┼┌╓╞╦╞╖╘ص┴╧╡─╨╨ئل���ثش─▄╖ً▒╗╜ظطîئل╔·«a╝┘╦ةت┴╙╦╡─╨╨ئل�����ث┐▀╩╟âHءï│╔╔·«a╝┘╦�ةت┴╙╦╡─ىAéغ╨╨ئلث┐طt(yذر)»اآCءï���ةتطt(yذر)»اآCءï╣ج╫≈╚╦Tنm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╗ٌ┴╙╦����ثش╡سâHî╩ر┴╦ئل│ِ╩█╢°┘┘Iةتâخ┤µ╡─╨╨ئل�����ثش╩╟╖ً┐╔▒╗╒J╢ذ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���ث┐▀╩╟âHءï│╔غN╩█╡─ىAéغ╨╨ئلث┐╦╞╖╫تâ╘╔م╒ê╬╬╗╡─╣ج╫≈╚╦T����ثش╣╩╥ظ╩╣╙├╧ضمP╠ô╝┘▓─┴╧ٌ_╚ة╦╞╖┼·£╩╫C├≈╬─╝■╙├╙┌╔·«aةتغN╩█╦╞╖╡─���ثش─▄╖ً╓▒╜╙╒J╢ذئلة░╔·«aة▒ة░غN╩█ة▒╨╨ئل▒╛╔و�ث┐
┼c┤╦═شـr�ثشîت▀\▌¤ةتâخ┤µ����ةت▒ث╣▄��ةتض]╝─╡╚░ل╔·╨╨ئل╫≈ئل╔·«aةتغN╩█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╫ي╡─╣▓╖╕╝╙╥╘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ثش╥▓┐╔─▄┤µ╘┌╧ض«¤ûى}�ةث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�ثش╝┤╩╣╔╧╩ِ╨╨ئل╡─î╩ر╒▀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ةت┴╙╦���ثش╥▓▓ت▓╗▒╪╚╗┼c╔·«a╒▀���ةتغN╩█╒▀╨╬│╔نp╧ٌ╡─╖╕╥ظ£╧═ذثش╢°╚ق╣√╥╘╞ش├µ╣▓╖╕╒ô╠�ثش╙╓▓ت╬┤س@╡├└و╒ô╜ق┼cî╒╜ق╡─╣س╘╩╨╘│╨╒Jث╗┴و╥╗╖╜├µ�ثش╚ق▓╔╣▓╖╕╡─╧▐╓╞─î┘╨╘╒fثش╣▓╖╕╨╨ئل╡─╠┴P▀╘┌î┘|╔╧╙╨┘ç╙┌╒²╖╕╡─▀`╖ذ╨╨ئل╡─îشF�����ثش▀@╘┌ءO┤ٍ│╠╢╚╔╧ـ■╓╞╝sîخ╣▓╖╕╨╨ئل╡─╥(guذر)╓╞ةث╩┬î╔╧�����ثش╔╧╩ِ╨╨ئلîخ╙┌╝┘┴╙╦╡─╩╨êِ┴≈═ذ╢°╤╘����ثش═شء╙╛▀╙╨مPµI╥ظ┴xةث╘┌╜ؤ╙╔╩╨êِ┴≈═ذ╡╓▀_╧√┘M╒▀▀M╢°═■├{╔·├ⁿ����ةت╜ة┐╡╖ذ╥µ╡─╥ظ┴x╔╧ثش╔╧╩ِ╨╨ئل╡─╬ث║خ╨╘┐╔─▄▓╗╙┌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╨╨ئل���ثش╞غ╘┌شFî╓╨╙╓╜ؤ│ث│╩شFئلزأ┴ت╡─╨╨ئل┼c╖╕╥ظء╙ّB(tذجi)��ةث╛═┤╦╢°╒ô�����ثش╫≈ئلزM┴x╣▓╖╕╝╙╥╘╠┴P┐╔─▄▓ت▓╗─▄îشF║╧└و╢°│غ╖╓╡─╥(guذر)╓╞���ةث
▀^═∙����ثش╨╠╖ذîخ╙┌╦╞╖╖╕╫ي╨╨ئل╖╜╩╜╡─╥(guذر)╢ذ▀^╙┌▒╞╪╞����ثشâH╧▐╙┌╔·«a┼cغN╩█â╔╖N╨╨ئل���ثشîخ▀@â╔é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╡─╔╧╙╬�����ةت╧┬╙╬�ةت░ل╔·╗ٌ▀Bد╨╨ئل╡─مP╫تt├≈ي@╟╖╚▒���ةث╘┌┤╦┤╬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╡─╨▐╙╓╨�ثش╥╗╖╜├µ�ثش╘┌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╓╨╘ِ╝╙┴╦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�ةت┴╙╦╢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╟ل╨╬ثشîت╨╨ئل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╤╙╔ه╓┴╔·«a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╨╨ئل╡─║ٍ╢╦�ث╗┴و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��ثشt╘┌╨┬╘ِ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╓╨����ثشîخ╦╞╖╔م╒ê╫تâ╘╓╨╡─╞█ٌ_╨╨ئل╝╙╥╘┴╦╤a│غ╥(guذر)╓╞ةث▀@╩╣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│╔┴ت╖╢ç·┐╔╟░╥╞╓┴╔·«a���ةتغN╩█╓«╟░╡─╔م╒êî┼·┼c╫تâ╘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�����ةث╥╘╔╧╨▐╙�ثش▓╗âH╩╣▒╗╥(guذر)╓╞╡─╨╨ئل╖╜╩╜╕ⁿئل╢ضء╙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─╥(guذر)╓╞ىI╙ٌ┼c╖╢ç·╔╧╙^▓هثش╥▓╕ⁿئل╓▄╤╙╡╪╕▓╔w╡╜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╓≈╥ز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���ثش┐╔╓^╩╟╧ض«¤╖eءO╡─╫â╗»�ةث╡س─î█`و┐┤ثش╦╞╖╖╕╫ي═∙═∙╨╬│╔┴╦╖╓╣جç└├▄���ةت╟░║ٍ┼غ║╧╡─╖╕╫يµ£ùl╔ُ╓┴╖╕╫ي«aءI(yذذ)����ةث▀@╞غ╓╨�����ثش╓┴╔┘░ⁿ└ذ╤╨░l(fذة)�����ةت┼R┤▓îٌئ����ةتî┼·╫تâ╘�ةت╔·«aةتغN╩█����ةت▀\▌¤ةت┤µâخ����ةت╩╣╙├��ةت╒┘╗╪╡╚╕≈é▓╗═ش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�����ثش▓تءï│╔┴╦╥╗╖N╟░║ٍ╧ض▀B�ةت╛o├▄عـ╜╙╡─╙ّB(tذجi)▀^│╠����ةث╜ؤ▀^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╡─╨▐╙ثشîخ╦╞╖╡─╔م╒ê╫تâ╘���ةت╔·«a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┼c╩╣╙├╡╚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╥╤╨╬│╔╧ضّز╥(guذر)╖╢��ثش╡س╚╘╬┤╨╬│╔╚س┴≈│╠��ةتل]صh(huذتn)╩╜╡─╓▄╤╙╥(guذر)╓╞��ةث│²╔╧╩ِ▀\▌¤�����ةت┤µâخ╡╚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╡─╨╨ئل╚╘╥└┘ç╙┌╣▓╖╕╠┴P─ث╩╜═ظثشîخ╙┌╦╞╖╤╨░l(fذة)���ةت┼R┤▓îٌئ����ةت╒┘╗╪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┐╔─▄╡─╬ث║خ╨╨ئل╥▓═م╚سؤ]╙╨ىآ╝░�ةث
╥╘╦╞╖╒┘╗╪ئل└²ةث▀@╥╗╓╞╢╚╡─╓≈╥ز─┐╡─╘┌╙┌��ثش«¤╦╞╖│ِشF┴╦╥╗╢ذ╡─┘|┴┐╚▒╧▌ـr�ثشّز═ذ▀^╒┘╗╪┤ن╩ر▒▄├ظيLنU┼côp║خ╜Y╣√╡─▀M╥╗▓╜¤U┤ٍ����ةث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82ùl├≈┤_╥(guذر)╢ذث║ة░╦╞╖┤µ╘┌┘|┴┐ûى}╗ٌ╒▀╞غ╦√░▓╚سن[╗╝╡─ثش╦╞╖╔╧╩╨╘S┐╔│╓╙╨╚╦ّز«¤┴ت╝┤═ث╓╣غN╩█�ثش╕µ╓ز╧ضمP╦╞╖╜ؤبI╞ٍءI(yذذ)║═طt(yذر)»اآCءï═ث╓╣غN╩█║═╩╣╙├ثش╒┘╗╪╥╤غN╩█╡─╦╞╖��ثش╝░ـr╣سل_╒┘╗╪╨┼╧ت�����ثش▒╪╥زـrّز«¤┴ت╝┤═ث╓╣╔·«aثش▓تîت╦╞╖╒┘╗╪║═╠└و╟لؤr╧ٌ╩ة��ةت╫╘╓╬à^(qذ▒)�����ةت╓▒▌ب╩╨╚╦├ً╒■╕«╦╞╖▒O(jiذةn)╢╜╣▄└و▓┐لT║═╨l(wذذi)╔·╜ة┐╡╓≈╣▄▓┐لTêٍ╕µ�����ة����ثة▒╘┌╞غ║ٍ╡─╡┌135ùl╓╨ثش╕ⁿ▀M╥╗▓╜├≈┤_┴╦╘┌▒O(jiذةn)╣▄▓┐لT╪ا┴ى╒┘╗╪╢°╛▄▓╗╒┘╗╪ـr�����ثش┐╔╩ر╥╘┴P┐ى�����ةت╡ُغN╦╞╖┼·£╩╫C├≈╬─╝■�����ةت╦╞╖╔·«a╘S┐╔╫Cةت╦╞╖╜ؤبI╘S┐╔╫C╡╚╠┴P┤ن╩ر��ةث╛═─┐╟░╡─╓╞╢╚╘O╙ïو┐┤�����ثش╧ضمP╦╞ٍ╛▄▓╗╒┘╗╪╙╨╚▒╧▌╡─╦╞╖ـr�ثشâH┐╔─▄╪ôô·╨╨╒■╪ا╚╬ثش╢°اo│╨ô·╨╠╩┬╪ا╚╬╓«ّ]���ةث╡سûى}╩╟���ثش╥╗╖╜├µثش«¤╦╞╖┤µ╘┌┘|┴┐╚▒╧▌╗ٌ╞غ╦√░▓╚سن[╗╝ـr����ثش╚╬╞غ┴≈═ذ╢°╛▄▓╗╒┘╗╪�����ثشي@╚╗╛▀╙╨╬ث║خ╣س▒è╔·├ⁿ╜ة┐╡╖ذ╥µ╡─╓╪┤ٍ═■├{�����ث╗┴و╥╗╖╜├µثش╬ّ{╨╨╒■┴P┐ى���ةت╡ُغN╦╞╖┼·£╩╫C├≈╬─╝■�����ةت╦╞╖╔·«a╗ٌ╜ؤبI╘S┐╔▀@╨ر┤ن╩ر�����ثش╩╟╖ً╫ع╥╘╨╬│╔╙╨╨د═■ّ╪��ثشt▓╗اo╥╔ّ]�ةث╩┬î╔╧�ثش╧ضمP╓≈ٍw╥ٌ╔·«aةتغN╩█╙╨░▓╚سن[╗╝╡─╦╞╖╢°╓╞╘ه┴╦╖ذ╦∙▓╗╘╩╘S╡─يLنU���ثش▀M╢°╕╜نS╨╘╡╪«a╔·┴╦╖└╓╣يLنU¤U╔ت╡─╒┘╗╪┴x╒���ةث▀@╥╗┴x╒╝╚╛▀╙╨╜╠┴xîW╔╧╡─╘·î╗∙╡Aثش╙╓╛▀╙╨î╢ذ╖ذ╔╧╡─├≈┤_╕∙ô■����ةث«¤╧ضمP╦╞ٍ▒╗▒O(jiذةn)╣▄آCءï╪ا┴ى╒┘╗╪╢°╛▄▓╗╒┘╗╪ـr��ثش╚ق╣√┤╦╖N╛▄▓╗╒┘╗╪╡─╨╨ئل▀M╥╗▓╜îد╓┬┴╦يLنU╡─شFî╗»╗ٌ¤U┤ٍ╗»����ثشّز╛▀╙╨î┘|╡─╨╠╩┬┐╔┴P╨╘����ةث
ثذ╢■ثرة░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ة▒┼cة░غN╩█ة▒╡─مP╧╡
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╘┌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╓«║ٍ╛∙╘ِ╝╙┴╦╥╗┐ىمP╙┌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╢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╟ل╨╬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ةث─ùl╬─╡─ٍw╧╡╬╗╓├┐┤ثش╨┬╘ِ╡─▀@┐ى╥(guذر)╢ذ╩╟╕╜╓°╘┌╡┌141ùl����ةت╡┌142ùl╓«╓╨╡─ثش╥ٌ╢°╨ك╥ز┼c╟░┐ى╥(guذر)╢ذîخ╒╒└و╜ظ��ةث╙╔╙┌ة░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ة▒╡─╨╨ئل┼c╔·«a╨╨ئل╛ضنx▌^┤ٍ����ثشمP╫ت╓╪╨─▒ع╫╘╚╗┬غ╘┌╞غ┼cغN╩█╨╨ئل╡─مP╧╡╓«╔╧ةث
╘┌▀@╥╗ûى}╔╧��ثش╥╤╨╬│╔▓╗╔┘╧ضمP╥(guذر)╖╢�����ة�����ثة░â╔╕▀ة▒╘ق╘┌2001─م4╘┬10╚╒ة╢مP╙┌▐k└و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é╬┴╙╔╠╞╖╨╠╩┬░╕╝■╛▀ٍwّز╙├╖ذ┬╔╚َ╕╔ûى}╡─╜ظطîة╖╡┌6ùl╓╨╥(guذر)╢ذث║ة░طt(yذر)»اآCءï╗ٌ╒▀é╚╦����ثش╓ز╡└╗ٌ╒▀ّز«¤╓ز╡└╩╟▓╗╖√║╧▒ث╒╧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ç°╝╥ء╦£╩ةت╨╨ءI(yذذ)ء╦£╩╡─طt(yذر)»ا╞≈╨╡����ةتطt(yذر)╙├╨l(wذذi)╔·▓─┴╧╢°┘┘Iةت╩╣╙├��ثشîخ╚╦ٍw╜ة┐╡╘ه│╔ç└╓╪╬ث║خ╡─����ثش╥╘غN╩█▓╗╖√║╧ء╦£╩╡─طt(yذر)╙├╞≈▓─╫ي╢ذ╫ي╠┴P�ة���ثة▒ءOئلى╦╞╡─����ثشة░â╔╕▀ة▒╘┌2014─م═ذ▀^╡─ة╢مP╙┌▐k└و╬ث║خ╦╞╖░▓╚س╨╠╩┬░╕╝■▀m╙├╖ذ┬╔╚َ╕╔ûى}╡─╜ظطîة╖╡┌6ùl╓╨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ة░طt(yذر)»اآCءï�ةتطt(yذر)»اآCءï╣ج╫≈╚╦T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ةت┴╙╦╢°╙╨â¤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��ثش╗ٌ╒▀ئل│ِ╩█╢°┘┘I�����ةتâخ┤µ╡─╨╨ئلة▒���ثشّز▒╗╒J╢ذ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���ةث▒M╣▄┘|╥╔╓≈╥ز╝»╓╨╘┌ئل│ِ╩█╢°┘┘I��ةتâخ┤µ╡─╨╨ئل╩╟╖ًءï│╔غN╩█▀@╥╗ûى}���ثش╡سîنH╔╧�ثش╘┌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╟لؤr╧┬╙╨â¤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╨╨ئل─▄╖ً▒╗╜ظطîئلغN╩█ثش╥▓▓╗اo╥╔┴x����ةث┼c╔╧╩ِ╥(guذر)╢ذ╦╝┬╖╜╙╜ⁿ╡س╕ⁿئل╝ج▀M╡─ثش╩╟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19ùl���ةث╘ôùl╥(guذر)╢ذث║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╩╣╙├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�ثش░┤╒╒غN╩█╝┘╦�ةت┴ع╩█┴╙╦╡─╥(guذر)╢ذ╠┴Pة��ثة▒╘ôùl▓╗âH╓▒╜╙┬╘▀^┴╦îخ╓≈╙^├≈╓ز╡─╥ز╟ٍ����ثش╢°╟╥îخ╙┌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╩╟╖ً▒╗╙╨â¤╩╣╙├�ثش╥▓╕∙▒╛▓╗╙كىآ╝░�ةث
╫╨╝أ╩ط└و╔╧╩ِ╥(guذر)╖╢╚║┐╔╥╘░l(fذة)شFثش╘┌░╤╬╒ة░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ة▒┼cة░غN╩█ة▒╡─مP╧╡╔╧�����ثش╙╨╫éمPµI╥ز╦╪ث║ثذ1ثر╓≈╙^╔╧╩╟╖ً├≈╓ز��ث╗ثذ2ثر╬╝â┘┘I▀╩╟┘┘I▓ت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��ث╗ثذ3ثر╠ط╣ر╩╣╙├ـr╩╟╖ً╙╨â¤�ةث╘┌▀@╨رمPµI╥ز╦╪╡─╠└و╔╧ثش╔╧╩ِ╥(guذر)╖╢╡─ّB(tذجi)╢╚▓╗▒M╧ض═ش����ةث╘┌ة░â╔╕▀ة▒2001─م╡─╦╛╖ذ╜ظطî╓╨ثشîخ╥ز╦╪ثذ1ثر▓╔╚ة┐╧╢ذ╫╦ّB(tذجi)�ثشîخ╥ز╦╪ثذ2ثر▒و╩ِ─ث║²ثشîخ╥ز╦╪ثذ3ثرtؤ]╙╨ىآ╝░�ث╗╘┌ة░â╔╕▀ة▒2014─م╡─╦╛╖ذ╜ظطî╓╨ثشîخ╥ز╦╪ثذ1ثر▓╔╚ة┐╧╢ذ╫╦ّB(tذجi)����ثشîخ╥ز╦╪ثذ2ثر│╓╖ً╢ذّB(tذجi)╢╚����ثشîخ╥ز╦╪ثذ3ثر│╓┐╧╢ذّB(tذجi)╢╚����ث╗╢°╘┌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╨����ثشîخ╥ز╦╪ثذ1ثرثذ3ثرؤ]╙╨ىآ╝░ثشîخ╥ز╦╪ثذ2ثرt│╓┐╧╢ذ╫╦ّB(tذجi)����ةثîخ╙┌╥ز╦╪ثذ1ثر╢°╤╘ثشîW╜ق┼cî╒╜ق═ذ│ث│╓┐╧╢ذّB(tذجi)╢╚��ةث╥╗░ع╒Jئل���ثش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�ةت╡┌142ùlئل╣╩╥ظ╖╕╫ي����ثش╨╨ئل╚╦▒╪وأ╛▀╙╨îخ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├≈┤_╒J╓زثش╖╜─▄│╔┴ت╣╩╥ظ����ةث┤╦┤╬┴ت╖ذ╨▐╒²╥▓╒²├µ▓╔╝{┴╦═ذ╒f╙^ⁿcة�����ث┐╔╥è�����ثش╥ز╦╪ثذ2ثر┼cثذ3ثر╧╡╓≈╥زبⁿc╦∙╘┌��ةث
╘┌ة░â╔╕▀ة▒2001─م╦╛╖ذ╜ظطî╡─╡┌6ùl╩╟╖ً╧╡ى═╞╜ظطî╡─ûى}╔╧��ثشê├≈┐ش��ةتًT▄è╡╚╜╠╩┌╛∙╒Jئل�ثشîتة░┘┘Iة▒╗ٌة░╩╣╙├ة▒╥ـئلة░غN╩█ة▒ثش╩╟║┴اo╥╔û╡─ى═╞╜ظطî�ةث┼c╓«╧ضîخثش╟·╨┬╛├╜╠╩┌t╒Jئلثشة░┘┘Iة▒╩╟ة░غN╩█ة▒╡─îخ┴ت╨╨ئل�����ثش╚ق╣√âHîتة░┘┘Iة▒╘uâr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�ثشîنH╔╧▀Bى═╞▀m╙├╢╝╒▓╗╔╧����ثش╢°╩╟╦╛╖ذ╒▀╡─╥╗╖N│ض┬ع┬ع╡─┴ت╖ذ╨╨ئلةث╘┌╦√┐┤و��ثش▒╛╜ظطî╓╨ة░┘┘Iة▒┼cة░╩╣╙├ة▒╓«لg▓ت╖╟ôً╥╗مP╧╡���ثش╢°╩╟╝µ╛▀مP╧╡ثش╥ظ╬╢╓°ة░┘┘I▓ت╟╥╩╣╙├ة▒����ةث▀@╖Nة░┘┘I▓ت╩╣╙├ة▒╡─╨╨ئلî┘|╔╧╩╟╥╗╖N╖╟╡غ╨═╡─ة░غN╩█ة▒╨╨ئلثشة░â╔╕▀ة▒╡─╦╛╖ذ╜ظطîءï│╔¤Uê╜ظطî╢°╖╟ى═╞╜ظطî����ةث┤╦╠ثش╖╓╞ق«a╔·╡─╕∙▒╛╘ص╥ٌ╘┌╙┌��ثشîخ╙┌ة░┘┘Iة▒┼cة░╩╣╙├ة▒╡╜╡╫╩╟ôً╥╗مP╧╡▀╩╟╝µ?zhذذn)غمP╧╡╙╨▓╗═ش└و╜ظثش▀M╢°���ثشîخ▀@╖N╗∙╡A╨╘╩┬î┼cغN╩█╨╨ئل╓«لg╡─مP╧╡«a╔·┴╦▓╗═ش└و╜ظ�ةثي@╚╗��ثشîت╬╝â╡─ة░┘┘Iة▒╥ـ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�ثش╩╟┐ق╚ن┴╦îخ┴ت╒Z╘~╡─║╦╨─╒Z┴x╖╢ç·����ثش├≈ي@│ش│ِ┴╦ة░غN╩█ة▒╡─╬─┴x╔غ│╠ثش▓تءï│╔┴╦│ش╘╜╜ظطîآض╧▐╡─î┘|┴ت╖ذ╨▐╕─��ةث▀@╥▓╒²╩╟╔╧╩ِة░â╔╕▀ة▒2014─م╦╛╖ذ╜ظطî╓«╡┌6ùlيû╩▄┘|╥╔╡─╘ص╥ٌ╦∙╘┌�ةث╘ôùl╥(guذر)╢ذثشئل│ِ╩█╢°┘┘I���ةتâخ┤µ╡─╨╨ئل╥▓ّز▒╗╒J╢ذ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���ثش╢°îنH╔╧▀@╨ر╨╨ئل╓┴╢ضءï│╔غN╩█╡─ىAéغ╨╨ئل��ةث
╕ⁿ╛▀╠َّ≡(zhذجn)╨╘╡─ûى}╩╟���ثش┘┘I▓ت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�����ثش╩╟╖ً┐╔▒╗╜ظطîئلغN╩█�ث┐╠╪e╩╟ثش╚ق╣√┼c╥ز╦╪ثذ3ثر╜Y║╧╞≡و╙^▓ه����ثش┘┘I▓ت╙╨â¤╡╪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ثش─▄╖ً▒╗╜ظطîئلغN╩█��ث┐╚ق╣√─╜ظطî│ِ┼_ـrثذ2001─م�ةت2014─مثر╡─طt(yذر)╦╓╞╢╚┐╝┴┐ثش▓╗âHطt(yذر)»ا╞≈╨╡���ةتطt(yذر)╙├║─▓─┼c╨l(wذذi)╔·▓─┴╧╩╟╙╨â¤╡╪╠ط╣ر╜o▓ة╗╝╩╣╙├ثش╢°╟╥╦╞╖▒╛╔و╥▓╘╩╘S╝╙│╔▓ت╙╨â¤╠ط╣ر����ةثîخ╙┌طt(yذر)»ا╞≈╨╡╢°╤╘ثش▒M╣▄╩╟╒√ٍw┘╚ن����ةت╖╓┤╬╩╣╙├ثش╡س╝┤╩╣îت╒√ٍw┘╚ن│╔▒╛ةت╖╓▓≡╩╣╙├┤╬¤╡���ةت╞≈╨╡║─ôp┼c╒█┼f╡╚╥ٌ╦╪┐╝ّ]╘┌â╚��ثش▀@╖N╙╨â¤╩╣╙├╚╘╚╗ـ■«a╔·└√إآ��ث╗╢°îخ╙┌╦╞╖┼cطt(yذر)╙├║─▓─╢°╤╘�ثش╕ⁿ╩╟└√إآءO╕▀����ةث╥ٌ┤╦ثش▒╛╬─âA╧ٌ╙┌╒Jئل�����ثش╘┌«¤ـr╡─╒Z╛│╧┬��ثش┐╔îت┤╦╖N┘▀M║ٍ╙╨â¤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╨╨ئل╜ظطî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ةث
╡س╓╡╡├╫ت╥ظ╡─╩╟ثششF╧┬╡─طt(yذر)»اصh(huذتn)╛│┼c╓╞╢╚ٍw╧╡╥╤╜ؤ░l(fذة)╔·┴╦║▄┤ٍ╡─▐D╫â��ةث─2017─م7╘┬1╚╒╞≡����ثش╘┌╚سç°╦∙╙╨╣س┴تطt(yذر)╘║═╞╨╨╦╞╖┴ع╝╙│╔╓╞╢╚�����ثش╝┤╫║ُ╦∙╙╨╦╞╖��ةتطt(yذر)╙├║─▓─▓╗╘╩╘S┘╚ن║ٍ╘┘╝╙│╔╠ط╣ر╜o╗╝╒▀╩╣╙├����ةث╛▀ٍw╡╜╦╞╖╢°╤╘����ثش▒M╣▄┐╔╖╓ئلطt(yذر)▒ث╦╞╖║═╖╟طt(yذر)▒ث╦╞╖ثش╙╓┐╔▀M╥╗▓╜╝أ╖╓ئل╝╫�����ةت╥╥��ةت▒√╚²ى╦╞╖�ثش╡س╞غ╓≈╥زà^(qذ▒)e╘┌╙┌êٍغN╞≡╕╢╛�����ةتêٍغN▒╚└²▓╗═ش��ةثîخ╙┌طt(yذر)╘║╢°╤╘ثش▓╗╣▄╦╞╖│╔▒╛╘┌ç°╝╥┼c╗╝╒▀╓«لg╚ق║╬╖╓ô·����ثش╠ط╣ر╦╞╖╣ر╚╦╩╣╙├▀@╥╗╨╨ئل┐═╙^╔╧▓╗«a╔·└√إآثش╓≈╙^╔╧╥▓▓╗┤µ╘┌╓≡└√─┐╡─���ثش╥ٌ╢°نy╥╘▒╗╜ظطî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�ةث▓╗▀^�ثش┴ع╝╙│╔╓╞╢╚╥▓╙╨└²═ظ���ةث▒╚╚ق��ثش╞غ╘┌╦╜┴تطt(yذر)╘║╗ٌ╞غ╦√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┐╔─▄▓ت▓╗▀m╙├����ثش╘┌╣س┴تطt(yذر)╘║â╚▓┐╡─╫╘┘M╦╖┐╥▓┐╔▒ث│╓╝╙│╔����ةت▓╗╩▄╒╨ء╦âr╕ً╙░وّةث┤╦═ظ�����ثش▓┐╖╓╡╪╖╜╥(guذر)╢ذثش╝┤╩╣╩╟╣س┴تطt(yذر)╘║����ثشîخ╙┌╓╨╦ىw┴ثرةت╓╨╦╙░ر╡╚┐╔╘╩╘S15%╡─╝╙│╔����ةث╘┌╔╧╩ِ└²═ظêِ║╧ثش╚ق┘▀M╦╞╖║ٍ╘┘╙╨â¤╡╪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��ثش╚╘┐╔▒╗î┘|╨╘╡╪╜ظطî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��ةث
╚ق┤╦┐┤و���ثش╘┌«¤╟░╡─طt(yذر)╦ٍw╧╡╧┬ثش╨┬╘ِ╡─ة░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����ثش╢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ة▒▀@╥╗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ثش▒M╣▄┼cغN╩█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╖╕╫ي╡─╥(guذر)╓╞ىI╙ٌ╚╘╙╨╓╪»Bثش╡س╞غ╜╗╝»îنH╔╧ءOئل╙╨╧▐�����ةث╬╥éâّز«¤═╞╢ذ�ثش┴ت╖ذ╒▀╥╤│غ╖╓╡╪╫ت╥ظ╡╜┴╦┤╦╖Nطt(yذر)╦ٍw╓╞║═╧╡╜yصh(huذتn)╛│╡─╫â╗»ثش╞غ╨┬╘O┤╦┐ى╡─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┼c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����ثشّز├≈ي@╙╨e╙┌╟░┐ى╡─غN╩█╝┘╦ةت┴╙╦╨╨ئل����ثش╖ًt╝┤ءï│╔┴ت╖ذ┘Y╘┤╡─└╦┘Mةث╥▓╥ٌ┤╦��ثش▀@â╔┐ى╥(guذر)╢ذ╝╚╖╟╟░┐ى╡─╫ت╥ظ╨╘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ثش╥▓╥ٌ╚▒╖خ¤M╓╞╗∙╡A╢°╖╟╞غ¤M╓╞╨╘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╢°╩╟╘┌╥(guذر)╖╢╥ظêD┼c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╔╧├≈ي@╙╨e╡─╨┬╘O╫ي├√���ثش┐╔▒╗╖Qئلة░╠ط╣ر╝┘╦╫ية▒ة░╠ط╣ر┴╙╦╫ية▒�ةث▀@â╔وù╫ي├√┼cغN╩█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╖╕╫ي╡─╓≈╥زà^(qذ▒)e╘┌╙┌ث║ثذ1ثر▒╛╫يئل╠╪╩ظ╓≈ٍwثش╝┤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��ثش╢°غN╩█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╖╕╫ي╡─╓≈ٍwtئل╦╞╖╔·«a╒▀┼cغN╩█╒▀ث╗ثذ2ثر▒╛╫ي╘┌╓≈╙^╖╜├µ▓ت▓╗╥ز╟ٍ╥╘╖╟╖ذبI└√ئل─┐╡─�ثش╢°╘┌غN╩█╝┘╦ةت┴╙╦╖╕╫ي╓╨��ثشt═ذ│ث╥╘╖╟╖ذبI└√ئل─┐╡─��ث╗ثذ3ثر┐═╙^╡─╨╨ئل╖╜╩╜╔╧╡─à^(qذ▒)e���ةث▒╛╫ي╓≈╥ز╥(guذر)╓╞îت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╨╨ئل�ثش▀@╥╗╨╨ئل╘┌╒√é╦╞╖┴≈═ذ╡─µ£ùl╔╧ثش═ذ│ث╠╙┌╔·«a��ةتغN╩█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╓«║ٍ����ثش╢°غN╩█╝┘╦�ةت┴╙╦╖╕╫ي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╓╪╨─t╘┌╙┌غN╩█╨╨ئل▒╛╔وةث┤╦═ظ�����ثش▒╛╫ي╓╨╡─╠ط╣ر╩╣╙├╨╨ئل����ثش┐╔─▄╩╟╙╨â¤╡─ثش╥ض┐╔─▄╩╟اoâ¤╡─��ةث╚ق╣√╘┌├≈╓زئل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╟لؤr╧┬╙╨â¤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�����ثش┐╔─▄┼cغN╩█╝┘╦ةت┴╙╦╨╨ئل╨╬│╔╕é║╧��ةث┤╦ـr���ثش╥ٌ╖ذ╢ذ╨╠═م╚س╧ض═ش�����ثش┐╔╕∙ô■╞غ╙ض╥ز╝■╡─إM╫ع╟لؤrثذ╚ق╓≈ٍw╥ز╝■ثرôً╥╗╫ي├√▀m╙├�����ةث
ثذ╚²ثر▀z┴َ╡─ûى}
╚ق╔╧╦∙╩ِ�����ثش╘┌ٍw╧╡╬╗╓├║═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╔╧�����ثشة░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���ةت┴╙╦ثش╢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ة▒╛▀╙╨▓╗═ش╙┌غN╩█╝┘╦�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╖╕╫ي╡─╢ذ╬╗ثش╛▀╙╨زأ┴ت╘O╓├╡─▒╪╥ز╨╘┼c╥(guذر)╖╢┐╒لg�ةث╡س╩╟ثش─╘ô╥(guذر)╢ذ╡─╛▀ٍw▒و╩ِو┐┤�ثش╚╘┤µ╘┌▓╗╔┘╥╔┴xثش╨ك╥ز▀M╥╗▓╜╝أ╓┬│╬╟ف┼c╒f├≈���ةث
1. ة░╩╣╙├ة▒╡─║ش┴x
▓╗نy░l(fذة)شFثش╘┌╨┬╘ِ╡─╘ô┐ى╥(guذر)╢ذ╓╨��ثش┤µ╘┌â╔╠ة░╩╣╙├ة▒����ةث╥╗╠╩╟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ة▒╓╨╓«ة░╩╣╙├ة▒ثش┴و╥╗╠t╩╟ة░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ة▒╓╨╓«ة░╩╣╙├ة▒�ةثûى}╩╟ثش▀@â╔╠ة░╩╣╙├ة▒╩╟╖ً╛▀╙╨═م╚س╧ض═ش╡─╥ظ║ص��ث┐
╥╗░ع╒Jئل����ثش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ة▒╛▀╙╨VةتزMâ╔┴x�ةثزM┴x╡─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╝┤ئلطt(yذر)╘║���ثش╢°V┴x╡─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t░ⁿ└ذطt(yذر)╘║ةتïD╙╫▒ث╜ة╘║����ةت╝▓▓ةىA╖└┐╪╓╞╓╨╨─ةت╖└╥▀╒╛����ةت╤ز╖└╒╛ةتضl(xiذةng)µé(zhذذn)╨l(wذذi)╔·╘║��ةت┤ف╨l(wذذi)╔·╩╥�����ةت╔قà^(qذ▒)╨l(wذذi)╔·╖■╒آCءï�����ةت╙ï╔·╖■╒╒╛�ةت╜غ╢╛╦∙╡╚╬╬╗ةث╘┌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╨���ثشنm╚╗╩╣╙├┴╦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ة▒▀@╥╗╖╢«ب��ثش╡س▓ت╬┤îخ▀@╥╗╖╢«ب╡─â╚║ص┼c═ظ╤╙╝╙╥╘├≈┤_╜ق╢ذ�ةث╚ق╣√─╘ô╖ذ╡─ٍw╧╡▒│╛░┼c▀m╙├╟ل╛│╙^▓هثش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ة▒t╜ؤ│ث┼c╦╞╖╤╨╓╞�ةت╔·«aةت╜ؤبI���ةت▒O(jiذةn)╣▄╬╬╗╡╚╧ض╠ط▓ت╒ô��ثش┐╔╥è��ثش┴ت╖ذ╒▀╓≈╥ز╩╟╘┌╦╞╖┴≈═ذ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╡─╜╟╢╚و┐╝ّ]ة░╩╣╙├ة▒╖╢«بةث▀M╥╗▓╜╡╪�����ثش╕∙ô■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92ùl╡─╥(guذر)╢ذث║ة░طt(yذر)»اآCءïّز«¤ê╘│╓░▓╚س╙╨╨د��ةت╜ؤإ·║╧└و╡─╙├╦╘صt����ثش╫ً╤ص╦╞╖┼R┤▓ّز╙├╓╕îد╘صtةت┼R┤▓╘\»ا╓╕─╧║═╦╞╖╒f├≈ـ°╡╚║╧└و╙├╦��ثشîخطt(yذر)ا╠╖╜����ةت╙├╦طt(yذر)ç┌╡─▀m╥╦╨╘▀M╨╨î║╦�����ةثطt(yذر)»اآCءï╥╘═ظ╡─╞غ╦√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��ثشّز«¤╫ً╩╪▒╛╖ذ╙╨مPطt(yذر)»اآCءï╩╣╙├╦╞╖╡─╥(guذر)╢ذ���ةثة▒╙╔┤╦┐╔╥è�����ثش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╓╨╡─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╗∙▒╛╔╧╩╟╚ة╞غV┴x�ةث
╩┬î╔╧ثشاo╒ô╩╟║╬╖N╥ظ┴x╡─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�ثش╛═╞غ╦∙╠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ةت╡╪╬╗┼c┬أ─▄╢°╤╘╛∙╛▀╙╨ى╦╞╨╘��ةث╥ض╝┤�����ثش╩╟╥╘ىA╖└�ةت╘\¤ض����ةت╓╬»ا╝▓▓ة╗ٌ╒{╜ظ╔·└وآC─▄ئل─┐╡─��ثش╝»╓╨╡╪╧ٌ╩▄╦╚╦╠ط╣ر╦╞╖▓ت░l(fذة)ô]╦╞╖╓«╣خ╨د╡─╙├╦╜M┐ù�ةث╥ٌ┤╦ثش▀@└ي╡─ة░╩╣╙├ة▒����ثش╩╟╥╗╖N└√╙├ةت░l(fذة)ô]╦╞╖╓«╣╠╙╨╣خ─▄┼c»ا╨د╡─╨╨ئل�����ثش╒²╦∙╓^ة░▒╛و╥ظ┴x╔╧╡─╩╣╙├ة▒���ةثوء╓°▀@╥╗├}╜jثش╚ق╙√▒ث│╓╕┼─ى╔╧╡─╥╗╓┬╨╘�ثشة░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ة▒╓╨╡─ة░╩╣╙├ة▒ثش╛═ّز╘ô╥ظ╬╢╓°┼cة░╩ر╦ة▒╧ضîخّز╥ظ┴x╔╧╡─ة░╙├╦ة▒��ةث╥▓╝┤�����ثش═ذ▀^╖■╙├╦╬يثش░l(fذة)ô]╦╬ي╣╠╙╨╡─ىA╖└�����ةت╘\¤ض����ةت╓╬»ا╝░╒{╜ظ╔·└وآC─▄╡─╣خ╨دةث╡سûى}╩╟�ثش╚╬║╬╩┬╬ي╡─╨د╙├╢╝╩╟╢ض╘ز╡─ةث╬غ╞≈▒╛و╥ظ┴x╔╧╡─╙├═╛╩╟أتé√��ثش╡س╥▓┐╔╙├╥╘╜╗ôQ╪¤╬ي���ةث═ش└و��ثش╦╬ي│²┴╦╞غ▒╛و╡─طt(yذر)╙├╣خ─▄═ظ��ثش╥▓┤µ╘┌ة░îْ╖║╥ظ┴x╔╧╡─╩╣╙├ة▒┐╔─▄���ةث└²╚قثشîت┴╙╦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║ٍ�ثش╙ك╥╘▀M╥╗▓╜╝╙╣ج▓ت═╞╧ٌ╩╨êِةث▀@└يثش╦√╚╦╡─╩╣╙├╙├═╛▓ت▓╗╥╗╢ذ╧▐╙┌╓▒╜╙╖■╙├╦╬ي���ةث
│²┴╦ة░▒╛و╥ظ┴x╔╧╡─╩╣╙├ة▒┼cة░îْ╖║╥ظ┴x╔╧╡─╩╣╙├ة▒╓«═ظ����ثش▀┤µ╘┌ة░╒√ٍw╨╘╡─╩╣╙├ة▒┼cة░╖╓▓≡╨╘╡─╩╣╙├ة▒╓«╖╓�����ةث║┴اo╥╔û����ثش╛═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îخ╧ٍ╢°╤╘ثش╦╬ي╒√ٍwثذ║ش╦╬ي▒╛ٍw�ةت░ⁿ╤bةت╒f├≈ـ°╡╚ثر╗ٌ╒▀╦╬ي▒╛ٍwاo╥╔ّز▒╗║ص╔w╘┌â╚����ةث╡س╫≈ئل╦╬ي▒╛ٍw╡─╕╜î┘╬يثش╚ق╦╞╖░ⁿ╤b╗ٌ╒f├≈ـ°╡╚╩╟╖ً▒╗░ⁿ║ش╘┌â╚�����ثشt▓╗اo╥╔û�����ةث╧ضمPî╫C╒{▓لي@╩╛��ثش═ذ▀^╧ٌطt(yذر)╘║╣ج╫≈╚╦T╩╒┘╡─═╛╜����ثشس@╡├╒²╥(guذر)╦╞╖╡─░ⁿ╤bةت╒f├≈ـ°╡╚╙├╙┌╓╞╩█╝┘╦╡─╨╨ئل▌^ئل╢ض░l(fذة)���ةث┼c╓«ى╦╞�����ثش╚ق╣√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╣ج╫≈╚╦T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ثذ╚ق╫â┘|╡─╦╞╖ثر╗ٌ┴╙╦ثذ╚ق▒╗╬█╚╛╡─╦╞╖ثر�����ثش╚╘îت▀@╨ر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░ⁿ╤b╗ٌ╒f├≈ـ°╠ط╣ر╜o║┌╫≈╖╗╝╙╥╘╩╣╙├�ثش╩╟╖ً╠╙┌▒╛┐ى╡─╠┴P╖╢ç·╓«â╚����ث┐
╔╧╩ِûى}╚ق║╬╠└وثش╙╨┘ç╙┌╦╛╖ذ╜ظطî┼cîW└و╤╨╛┐╡─▀M╥╗▓╜│╬╟فةث╘┌▒╛╬─┐┤و����ثشة░╠ط╣ر╝┘╦╫ية▒┼cة░╠ط╣ر┴╙╦╫ية▒╡─╨┬╘Oثش╚╘╚╗╩╟╗∙╙┌îخ╙╨╚▒╧▌╦╞╖╡─┴≈═ذ╣▄╓╞╢°╘O��ثش▓ت├µ╧ٌ╣س▒è╡─╔·├ⁿ╜ة┐╡╖ذ╥µ╠ط╣ر▒ث╒╧�ةث╛═┤╦╢°╤╘ثش«¤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░l(fذة)شF╧╡╝┘╦╗ٌ┴╙╦╓«║ٍ��ثش╛═ّز«¤╧ٌ╔╧╝ë╗ٌ╧ضمP╦╞╖▒O(jiذةn)╣▄▓┐لTàRêٍ��ثش╙╔┤╦¤╪¤ض╙╨╚▒╧▌╦╞╖▀M╥╗▓╜┴≈═ذ╡─┐╔─▄����ةث╥ٌ┤╦ثش╝┤╩╣▓ت╖╟└√╙├╦╞╖▒╛و╙├═╛╓«╩╣╙├���ثش╚ق└√╙├╦╞╖╓«╜╗ôQâr╓╡�����ةت╝╙╣جâr╓╡╡╚╩╣╙├╨╨ئل�ثش╥▓╚╘╚╗┤┘▀M┴╦╙╨╚▒╧▌╦╞╖╡─┴≈═ذ��ثش▓تîخ╣س▒è╓«╜ة┐╡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«a╔·═■├{ثش╙╨▒╪╥زîت╞غ╝{╚ن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����ةث╡س╛═╖╓▓≡╩╣╙├╢°╤╘ثش╚ق╣√âHâH╩╟îت╝┘╦╗ٌ┴╙╦╡─░ⁿ╤b����ةت╒f├≈ـ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ثشt▓╗╥╦╝{╚نâ╔╫ي╓«╠┴P╖╢ç·����ةث▀@╥╗╖╜├µ╩╟╥ٌئلثش─┴ت╖ذ╡─╬─╫╓▒و╩ِ┐┤���ثش┴ت╖ذ╒▀╘┌ة░╢°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ة▒╓╨╩ة┬╘┴╦┘e╒Z����ثشّز«¤╒Jئل╘ô┘e╒Z┼c╟░╢╬╥╗╓┬���ةث╥ض╝┤���ثش├≈╓ز╡─îخ╧ٍ┼c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îخ╧ٍّز▒ث│╓╥╗╓┬�����ثش╛∙ئل╝┘╦�ةت┴╙╦����ةث╚ق╣√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╡─▓ت▓╗╩╟╝┘╦ةت┴╙╦▒╛╔و����ثش╢°╩╟╞غ░ⁿ╤bةت╒f├≈ـ°╡╚╕╜نS╬ي�ثشt┤µ╘┌îخ╧ٍ╡─▐DôQ║═╙╬╥╞ثش▓ت╙╨│ش│ِ╬─┴x╔غ│╠╓«╙▌�����ةث┴و╥╗╖╜├µt╩╟╥ٌئل�ثش─î┘|╜╟╢╚┐╝┴┐ثش▀@╖N╨╨ئلîخ╣س▒è╔·├ⁿ����ةت╜ة┐╡╖ذ╥µ╦∙╘ه│╔╓«═■├{�����ثش╘┌╛o╞╚╗»ةتشFî╗»╡─│╠╢╚╔╧▌^╡═���ثش╥ٌ╢°┼câ╔╫ي╡─╥(guذر)╖╢▒ث╫o─┐╡─▓╗╖√����ثش╚▒╖خî┘|╡─╠┴P▒╪╥ز╨╘��ةث
2.╓≈ٍw╡─╥╔û
╚ق╣√─┴ت╖ذ▒و╩ِو┐┤�ثشة░╠ط╣ر╝┘╦╫ية▒┼cة░╠ط╣ر┴╙╦╫ية▒╡─╖╕╫ي╓≈ٍwّز╩╟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ة▒ةث▀@╥╗╥(guذر)╢ذ┐┤╦╞├≈┤_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╚╘┤µ╘┌╥╔û���ةث
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��ثش▀@└ي╡─╚╦T╛┐╛╣║╬╓╕���ثش╘┌â╚║ص┼c═ظ╤╙╔╧▓ت▓╗╟ف╬·��ةث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╖ذ╢ذ┤·▒و╚╦�����ةت╓≈╥ز╪ô╪ا╚╦��ةت╓▒╜╙╪ô╪ا╡─╓≈╣▄╚╦T���ةت╞غ╦√╓▒╜╙╪ا╚╬╚╦Tّز▒╗░ⁿ║ش╘┌â╚╣╠اo╥╔ûثش╡س╞غ╦√┼c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▓تاo╣╠╢ذ╣═éٌمP╧╡╗ٌ╓▒╜╙╣═éٌمP╧╡╡─╚╦T����ثش╚ق╟┌نs╣جةت╫o╣ج╡╚╩╟╖ً░ⁿ║ش╘┌â╚�ثشt╙╨╥╗╢ذ╡─╜ظطî┐╒لgةث╘┌طt(yذر)╘║â╚���ثش╙╨╘S╢ض╪ô╪ا╨l(wذذi)╔·┤ٌْ▀����ةت▒ثإ��ةت║ٍ╟┌╣ج╫≈╡─┼Rـr╣═éٌ╚╦Tثش▀@╨ر╚╦T╥ٌ┼cطt(yذر)╔·�����ةت╫o╩┐لL╞┌╥╗╞≡╢°╨╬│╔╥╗╢ذ╡─╨┼┘çمP╧╡�ثش╘┌╖╟│ثـr╞┌┼cّز╝▒بىّB(tذجi)╧┬ثش┐╔─▄╩▄═╨╧ٌ╗╝╒▀╗ٌ╦√╚╦╠ط╣ر╦╬ي�����ةث╢°طt(yذر)╘║╫o╣ج┼cطt(yذر)╘║��ةت╓╨╜ل╣س╦╛╓«لg┐╔─▄▓ت▓╗┤µ╘┌╓▒╜╙╣═éٌمP╧╡���ثش▒M╣▄╞غ╘┌طt(yذر)╘║╣ج╫≈ثش╟╥╛▀╙╨╥╗╢ذ╡─îثءI(yذذ)╫o└و╓ز╫R┼c╜ؤٌئ���ثش╡س┐╔─▄âHئل▓ة╚╦╗ٌ╝╥î┘╦∙╞╕╙├���ةث«¤▀@╨ر╚╦T├≈╓ز╧╡╝┘╦ةت┴╙╦às╚╘╧ٌ╗╝╒▀╗ٌ╦√╚╦╠ط╣ر╩╣╙├ـr����ثش╩╟╖ًءï│╔▀m╕ً╓≈ٍw����ث┐╘┌▒╛╬─┐┤و���ثشâ╔╫ي╓«╥(guذر)╖╢─┐╡─╘┌╙┌╟╨¤ض╦╞╖╘┌╩╣╙├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╡─┴≈═ذ╟■╡└�ثش╥╘▒ث╫o╣س▒è╜ة┐╡�����ةت╔·├ⁿ╖ذ╥µ����ثش╢°▓ت╖╟╗╝╒▀╓«╙┌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║╧└و╨┼┘çمP╧╡ةث▒M╣▄╔╧╩ِ╚╦T▓╗╩╟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╒²╩╜╛╓╞╚╦T���ثش╡س╞غ╠ط╣ر╝┘╦╗ٌ┴╙╦╣ر╦√╚╦╩╣╙├╓«╨╨ئل�ثش═شء╙╛▀╙╨╓╕╧ٌâ╔╫ي▒ث╫o╖ذ╥µ╡─شFî═■├{�ث╗═شـrثشîت╞غأw╚ن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╚╦Tة▒╥▓▓ت╬┤│ش│ِ╬─┴x╡─╔غ│╠�ةث╥ٌ┤╦ثش┐╔┐╝ّ]îت╞غ╫≈ئلâ╔╫ي╓«▀m╕ً╓≈ٍw����ةث
┴و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ثشâ╔╫ي╡─│╔┴ت╓≈ٍw╩╟╖ًâH╧▐╙┌╫╘╚╗╚╦ث┐╚ق╣√─┴ت╖ذ▒و╩ِ│ِ░l(fذة)�ثشي@╚╗╓╗─▄╙╔╚╦T╢°╖╟╬╬╗ءï│╔ثش╙╔┤╦┼┼│²┴╦╬╬╗╖╕╫ي╡─│╔┴ت┐╒لg���ةث╡سûى}╩╟����ثش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═م╚س╛▀╙╨╠ط╣ر╩╣╙├╓«╨╨ئل─▄┴خ┼c╥ظ╦╝╨╬│╔─▄┴خ�����ثش╥ض╙╨╓°î╩ر┤╦ى╨╨ئل╡─شFî┐╔─▄����ةث╘┌â╔╫ي╓╗─▄╙╔╫╘╚╗╚╦ءï│╔╡─╟░╠ط╧┬����ثش╝╚اo╖ذ╨╬│╔îخ╬╬╗╡─╢َ╓╞┴خ┼c═■ّ╪┴خثش╥▓┐╔─▄╩╣╡├╫╘╚╗╚╦╢▌╚ن╬╬╗╓«╢▄���ثش╜ك╙╔╬╬╗╓«أجو╤┌╫oî┘|╗»╡─é╚╦╨╨ئل��ةث╢°╟╥��ثش▀@ء╙╡─╘O╢ذ▓╗âH═╞╖ص┴╦╦╛╖ذ╜ظطî╓╨┐╧╒J╬╬╗╖╕╫ي╡─╙^ⁿc����ثش╥▓┼c╟░╓├╖ذ╡─╥(guذر)╢ذ▒│╡└╢°ًYةث╘┌ة░â╔╕▀ة▒2014─م═ذ▀^╡─ة╢مP╙┌▐k└و╬ث║خ╦╞╖░▓╚س╨╠╩┬░╕╝■▀m╙├╖ذ┬╔╚َ╕╔ûى}╡─╜ظطîة╖╡┌6ùl╓╨����ثش├≈┤_╥(guذر)╢ذة░طt(yذر)»اآCءïةتطt(yذر)»اآCءï╣ج╫≈╚╦T├≈╓ز╩╟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┴╙╦╢°╙╨â¤╠ط╣ر╜o╦√╚╦╩╣╙├ة▒ثشّز▒╗╒J╢ذئلة░غN╩█ة▒�ةث▀@╩╟│╨╒J┴╦طt(yذر)»اآCءï╫≈ئل╬╬╗│╔┴تâ╔╫ي╡─▀m╕ً╨╘ةث╢°╘┌2019─م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┌119ùl╓╨t╥(guذر)╢ذ��ثش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╩╣╙├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╡─�����ثش░┤╒╒غN╩█╝┘╦ةت┴ع╩█┴╙╦╡─╥(guذر)╢ذ╠┴Pة▒�����ثش╕ⁿ╩╟V╖║│╨╒J┴╦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î╩رى╦╞╨╨ئل╡─╨╨╒■▀`╖ذ─▄┴خ┼c╩▄╨╨╒■╠┴P─▄┴خ�����ةث╘┌╞غ║ٍ╡─╡┌124ùl╡┌3┐ى╓╨╕ⁿ├≈┤_╥(guذر)╢ذث║ة░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╩╣╙├╟░┐ى╡┌╥╗وù╓┴╡┌╬فوù╥(guذر)╢ذ╡─╦╞╖╡─��ثش╥└╒╒╟░┐ى╥(guذر)╢ذ╠┴P�ث╗╟ل╣إ(jiذخ)ç└╓╪╡─ثش╦╞╖╩╣╙├╬╬╗╡─╖ذ╢ذ┤·▒و╚╦�����ةت╓≈╥ز╪ô╪ا╚╦�ةت╓▒╜╙╪ô╪ا╡─╓≈╣▄╚╦T║═╞غ╦√╪ا╚╬╚╦T╙╨طt(yذر)»ا╨l(wذذi)╔·╚╦Tê╠(zhذز)ءI(yذذ)╫Cـ°╡─��ثش▀ّز«¤╡ُغNê╠(zhذز)ءI(yذذ)╫Cـ°����ةثة▒▀@╩╟├≈┤_îتîخ╬╬╗╡─╠┴P┼cîخ╫╘╚╗╚╦╡─╠┴Pà^(qذ▒)╖╓ل_و�����ةث╙╔┤╦┐╔╥èثش╚ق╣√╨╠╖ذ╔╧▓╗│╨╒Jâ╔╫ي╙╨╬╬╗╖╕╫ي╓«│╔┴ت╙ض╡╪����ثش▒ع╝╚نy╥╘╤╙└m(xذ┤)╓«╟░╡─╦╛╖ذé≈╜yثش╥▓نy╥╘┼c╨╨╒■╖ذ╥(guذر)▀M╨╨║╧└وعـ╜╙▓ت╨╬│╔╥(guذر)╓╞║╧┴خ�ةث
3.ة░├≈╓زة▒╡─└و╜ظ
╘┌ة╢╨╠╖ذة╖╡┌141ùlةت╡┌142ùl╡─▀m╙├╔╧�����ثش╓≈╙^╔╧╡─╒J╢ذ╥╗╓▒╖╟│ث└دنy�����ةث╘┌╦╛╖ذî█`╓╨�ثش╥ٌئلاo╖ذ╒J╢ذ╓≈╙^├≈╓ز╢°▓╗▓╢ةت▓╗╘V╗ٌ╜ذ╫h╣س░▓آCمP│╖░╕╡─╟لؤr╧ض«¤╞╒▒ل���ةث▒╚╚ق�ثش╧ضمPî╫C╒{▓لي@╩╛��ثش╜ⁿ─مو╔╧║ث╩╨لh╨╨à^(qذ▒)آz▓ه╘║╥ٌاo╖ذ╒J╢ذ╓≈╙^├≈╓ز╢°╜ذ╫h╣س░▓آCمP│╖░╕╡─╒╝▒╚╕▀▀_45%�ةث╙╔╙┌╓≈╙^╔╧╒J╫R╥ز╦╪╡─╒J╢ذنy╥╘╙ظ╘╜�ثش═شـr╦╛╖ذ┼╨¤ض╔╧╙╓┤µ╘┌╧ض«¤╒╧╡K�����ثش╘┌2009─م═ذ▀^╡─ة╢╫ى╕▀╚╦├ً╖ذ╘║�ةت╫ى╕▀╚╦├ًآz▓ه╘║مP╙┌▐k└و╔·«aةتغN╩█╝┘╦�ةت┴╙╦╨╠╩┬░╕╝■╛▀ٍwّز╙├╖ذ┬╔╚َ╕╔ûى}╡─╜ظطîة╖╡┌4ùl╓╨╥(guذر)╢ذث║ة░طt(yذر)»اآCءï╓ز╡└╗ٌ╒▀ّز«¤╓ز╡└╩╟╝┘╦╢°╩╣╙├╗ٌ╒▀غN╩█╡─ة▒ثش╚ق╖√║╧▒╛╫ي╞غ╦√ùl╝■�ثش┐╔╒J╢ذئلغN╩█╝┘╦╫يثش╡┌5ùltطءîخ┴╙╦╖╕╫ي╝╙╥╘ى╦╞╥(guذر)╢ذ��ةث▀@îنH╔╧╩╟îت╓≈╙^├≈╓ز╡─╖╢ç·�����ثش¤U╒╣╡╜┴╦ة░╓ز╡└ة▒┼cة░ّز«¤╓ز╡└ة▒â╔╖N╟ل╨╬����ةث▒M╣▄▀@╥╗╦╛╖ذ╜ظطî╥╤▒╗2014─م═ذ▀^╡─ة╢╫ى╕▀╚╦├ً╖ذ╘║ةت╫ى╕▀╚╦├ًآz▓ه╘║مP╙┌▐k└و╬ث║خ╦╞╖░▓╚س╨╠╩┬░╕╝■▀m╙├╖ذ┬╔╚َ╕╔ûى}╡─╜ظطîة╖╦∙U╓╣�����ثش╡س╙╔╙┌2014─م╜ظطî╓╨▓تاo╓≈╙^╒J╢ذ╡─╧ضمP╓╕╥²����ثشî█`╓╨╚╘╚╗╤╙└m(xذ┤)╓°╔╧╩ِ╡─╒J╢ذ╦╝┬╖ةث
╚ق║╬└و╜ظة░ّز«¤╓ز╡└ة▒����ثش╘┌î█`╓╨╥╗╓▒éغ╩▄ب╫hةث╛═îW└و╢°╤╘����ثشة░ّز«¤╓ز╡└ة▒ّز▒╗└و╜ظئل─│╖Nة░═╞╢ذ╡─╓ز╡└ة▒ثش▓ت│╨ô·╞≡£p▌p╣س╘VآCمP╫C├≈╪ôô·╡─î█`╣خ─▄���ةث╚╗╢°��ثشî█`╓╨îخ£p▌p╫C├≈╪ôô·╡─▀^╢╚╫╖╟ٍ����ثش═∙═∙ـ■╩╣ة░ّز«¤╓ز╡└ة▒╡─└و╜ظ▒╗«╗»���ةث└²╚ق�����ثش╥╗╖Nو╫╘╦╛╖ذî█`▓┐لT╡─╙^ⁿc╒Jئل��ثشة░╔·«a�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╝┘╦╫ي╡─├≈╓زّز«¤░ⁿ║ش╥╤╜ؤ╗ٌّز«¤╓ز╡└╧╡╝┘╦��ةت╥╤╜ؤّ╤╥╔╗ٌّز«¤ّ╤╥╔╧╡╝┘╦����ةت▓╗─▄┐╧╢ذ╗ٌ▓╗ّز┐╧╢ذ╧╡╒µ╦ثش╚╘╙ك╥╘╔·«a���ةتغN╩█╡─╨─└وبىّB(tذجi)ة▒��ةثûى}╘┌╙┌��ثشّز«¤ّ╤╥╔╧╡╝┘╦╢°îنH╔╧▓ت╬┤ّ╤╥╔��ةت▓╗ّز┐╧╢ذ╧╡╒µ╦╢°îنH╔╧às╙ك╥╘┐╧╢ذ╡─╟ل╨╬���ثش╩╟╘ص▒╛╥ظ┴x╔╧╡─▀^╩د╨─ّB(tذجi)ثش┼c╣╩╥ظ╙╨╓°╨╘┘|╔╧╡─▓ى«���ةث╚ق╣√╒f��ثش2014─مة░â╔╕▀ة▒╡─╦╛╖ذ╜ظطî╔╨╬┤├ôنx╣╩╥ظ╕┼─ى╡─╥╗░ع┐ٌ╝▄�����ثش╓╗╩╟îت╞غ╒J╫R╥ز╦╪¤Uê╡╪└و╜ظئلة░╓ز╡└ة▒┼cة░═╞╢ذ╡─╓ز╡└ة▒��ثش─╟├┤��ثش╔╧╩ِ└و╜ظt═╗╞╞┴╦╣╩╥ظ╕┼─ى╡─╥(guذر)╖╢ءï╘ه���ثش═ذ▀^╕─╫â╒J╫R╥ز╦╪╡─╡╪╬╗┼câ╚╚▌ثشîت╘ص▒╛╥ظ┴x╔╧╡─▀^╩د╟ل╨╬è╨╨╚√╚ن╣╩╥ظ╓«╓╨����ثش┐╔╓^ة░╕┼─ى╡─«╗»ة▒ةث
╩┬î╔╧����ثش╝┤╩╣╛═ة░ّز«¤╓ز╡└ة▒╢°╤╘ثش╒J╫R╥ز╦╪╡─═╞╢ذ╚╘وأ╓¤╔≈╢°ئل��ةث╥▓╝┤��ثش▓╗─▄╥ٌ╜╡╡═╫C├≈╪ôô·╡─╨ك╥ز�����ثش╢°▀^╖╓╜╡╡═îخ╗∙╡A╥ز╦╪╡─╥ز╟ٍةث╖ًt�����ثش╛═┐╔─▄╩╣═╞╢ذ╚▒╖خ║╧└و╗∙╡A���ثش╩╣╡├î┘|╥ظ┴x╔╧╡─▀^╩د▒╗═╡ôQ╒J╢ذئل╣╩╥ظ����ةث╛═┤╦╢°╤╘�ثش╗∙╡A╥ز╦╪▒╪وأ┼cة░╓≈╙^╔╧╡─├≈╓زة▒╛▀éغ╜ؤٌئ╥ظ┴x╔╧╡─╕▀╢╚╔w╚╗╨╘┬ô╧╡ثش▀@╩╟╒J╢ذ╨╨ئل╚╦╛▀╙╨╓≈╙^╒J╫R╡─┐═╙^╗»�����ةت║╧└و╗»▒و╒≈�ةث╚ق╣√╛▀éغ╗∙╡A╥ز╦╪ثشàs╥ز═╞╖ص╓≈╙^├≈╓ز╡─╛▀éغ��ثشّز«¤╩╟╥╘«│ث═▀╜ظ═ذ│ث����ثش╥╘└²═ظ═╞╖ص│ث╟ل����ةث
╛▀ٍw╡╜╣╩╥ظ╠ط╣ر╝┘╦��ةت┴╙╦â╔╫ي╢°╤╘��ثش┐╔═ذ▀^╧┬╩ِ╟ل╨╬╡─╛C║╧î▓لو┼╨¤ض╨╨ئل╚╦╩╟╖ً╧╡ة░ّز«¤╓ز╡└ة▒ث║ثذ1ثر╨╨ئل╚╦╡─╓ز╫R▒│╛░�����ثش░ⁿ└ذ╨╨ئل╚╦╡─╩▄╜╠╙²┬─أv����ةت╨╨ءI(yذذ)╜ؤٌئ���ةت╬╗┼ض╙û╜ؤأv╡╚╟لؤr�ث╗ثذ2ثر╨╨ئل╚╦╡─╟░┐╞┴╙█E�ثش╥ض╝┤ثش╨╨ئل╚╦▀^═∙╩╟╖ً┤µ╘┌ى╦╞╨╨ئل��ثش╩╟╖ً╥ٌى╦╞╨╨ئل╢°╩▄▀^╨╨╒■╠┴P����ةت╝o┬╔╠╖╓╡╚���ث╗ثذ3ثر╨╨ئل╚╦îخ╦╞╖╧ضمP┘Y┘|╬─╝■╡─┴╦╜ظ╟لؤrثش╥ض╝┤����ثش╨╨ئل╚╦╩╟╖ًîخ╞ٍءI(yذذ)╡─╦╞╖╔·«a╘S┐╔╫Cةت╦╞╖│ِS┘|┴┐آzٌئ║╧╕ًêٍ╕µـ°╡╚╝╙╥╘î║╦����ثش╚ق╧╡▀M┐┌╦╞╖ثش╩╟╖ًîخة╢▀M┐┌╦╞╖╫تâ╘╫Cة╖ة╢▀M┐┌╦╞╖آzٌئêٍ╕µـ°ة╖ة╢▀M┐┌╦╞╖═ذمP╬ة╖╡╚╝╙╥╘î║╦����ثش╩╟╖ً┴╦╜ظ╔╧╩ِ▓─┴╧╡─╟╖╚▒╗ٌ╨╬╩╜كخ┤├ث╗ثذ4ثر╨╨ئل╚╦îخ╦╞╖╨╬╩╜═ظ╙^╡─┴╦╜ظ╟لؤr�ثش╥ض╝┤ثش╨╨ئل╚╦╩╟╖ًîخ╦╞╖▀M╨╨═ظ╙^╨╬╩╜╡─î▓ل��ثش╩╟╖ً╓ز╧ج╦╞╖╘┌░ⁿ╤b��ةتء╦║ئ��ةت╒f├≈ـ°���ةتîث╙╨ء╦╫R╔╧╡─é╬╘ه�����ةت═┐╕─����ةت╝┘├░╡╚║██E┼c╚▒╧▌ث╗ثذ5ثر╨╨ئل╚╦îخغN╩█╟■╡└┼câr╕ً╡─┴╦╜ظ╟لؤr���ثش╥ض╝┤ثش╨╨ئل╚╦╩╟╖ً╓ز╡└╦╞╖╧╡╖╟╒²╥(guذر)╟■╡└┘╚ن��ثش╚ق─╖╟╖ذêِ╦∙╗ٌاo┘Y┘|╔╧╝╥┘╚ن╦╞╖����ثش╗ٌ╒▀╥╘▀h╡═╙┌╩╨êِ╡─âr╕ً┘╚نث╗ثذ6ثر╨╨ئل╚╦╡─«│ث╨╨ئل▒وشF���ثش╚ق╩╟╖ً┤µ╘┌îخ╦╞╖╡─ن[─غ╗ٌغNأد╨╨ئل��ثش╩╟╖ً┤µ╘┌┼c▒╗╠ط╣ر╒▀╓«لg╡─ن[▒╬╨╘╜╗╥╫╨╨ئل╡╚���ةث
╦─ةت╜Y╒Z
ة╢╨╠╖ذ╨▐╒²░╕ثذ╩«╥╗ثرة╖مP╙┌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╨▐╒²ثش▌^ئل╪╡╫╡╪╪ئ╪┴╦╖ذ╓╚╨ٌ╧ضîخ╜y╥╗╡─╘ص└و��ثش╘┌╒√ٍw╔╧ّز╘ô▒╗┐╧╢ذ���ةث╥╗╖╜├µ���ثش╦ⁿê╘│╓┴╦╨╠╩┬▀`╖ذ╨╘╘┌┼╨¤ض╔╧╡─╧ضîخ╨╘ثش╩╣╨╠╖ذ╔╧╝┘┴╙╦╡─╒J╢ذء╦£╩┼c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╘┌├≈├µ╔╧├ôع^����ث╗┴و╥╗╖╜├µثش╦ⁿ╙╓وءّز┴╦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╨▐╖ذ╙╧ٌ�����ثشçL╘çîت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┼c╣س▒è╜ة┐╡╔·├ⁿ╖ذ╥µ▀m«¤╖╓نx����ثش▓ت╜▀┴خ▒ث│╓╥(guذر)╖╢─┐ء╦╔╧╡─╝â╗»ةث▀M╥╗▓╜╡╪���ثش╦ⁿ╘çêD═╪╒╣║══م╔╞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┤ٌôَ╖╢ç·�����ثش▓ت╕▓╔w╔·«a����ةتغN╩█╓«═ظ╡─╔م╒ê╫تâ╘┼c╦╞╖╩╣╙├╡╚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ةث▀@╨ر╨▐╒²╩╣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▒ث╫o┐═ٍw���ةت╨╨ئلîخ╧ٍ���ةت╨╨ئل╖╜╩╜╡╚║╦╨─╥(guذر)╖╢╥ز╦╪╡├╥╘âئ(yذصu)╗»ثش╥▓╩╣╟░╓├╖ذ┼c▒ث╒╧╖ذ╡─àf╙مP╧╡╡├╡╜╕ⁿ║├╡─╒√ي���ةث
«¤╚╗����ثش╔╧╩ِ┼ش┴خ╚╘┤µ╘┌▀M╥╗▓╜╖┤╦╝╡─╙ض╡╪�����ةث╝┘┴╙╦╒J╢ذء╦£╩┼c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╡─├ôع^��ثش▓╗ّز▒╗└و╜ظئل─│╖N╜^îخ▓╗─▄àت╒╒╡─╜√┴ى��ثش╢°╓╗╩╟╥ظ╬╢╓°é╨╘╡─�����ةت╥(guذر)╖╢╨╘╛╨╩°╡─╦╔╜ë��ةث╞غ▓ت▓╗╖┴╡K╨╠╩┬╦╛╖ذ╓╨îخ╟░╓├╖ذء╦£╩╩┬î╔╧╡─àت╒╒��ثش═شـr��ثش╥ضئل╨╠╖ذ╔╧╡─╧ضîخ╗»┼╨¤ض┌A╡├▒╪╥ز┐╒لg��ث╗╨┬╘ِ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╓╨ة░╫ع╥╘ç└╓╪╬ث║خ╚╦ٍw╜ة┐╡╡─ة▒╡─╘O╢ذ��ثشt╩╣╦╞╖╣▄└و╓╚╨ٌ┼c╣س▒è╜ة┐╡╔·├ⁿ╖ذ╥µ╘┘╢╚╗ه═ش�ثش┴ى╚╦ءO╢╚▀z║╢ةث▀@▓╗╡س╩╣ة╢╦╞╖╣▄└و╖ذة╖┼c╨╠╖ذ╡─╖ذ╥µ╘O╓├▀ë▌ï╧ض╗ح╡╓مُ�ثش╢°╟╥┐╔─▄╩╣╟░╓├╖ذ╔╧╡─┴ت╖ذ╨▐╒²│╔╣√╣خ╠إ╥╗║êثشاo╖ذ╘┌▒ث╒╧╖ذ╔╧╡├╥╘┬غî����ثش╕ⁿîخ╦╛╖ذî█`╡─╛▀ٍw╒J╢ذ╠ط│ِ┴╦ç└╛■╠َّ≡(zhذجn)ةث═شـr��ثش─╥(guذر)╓╞╖╢ç·┼câ╚╚▌╔╧╙^▓ه���ثش╡┌142ùl╓«╥╗╥▓ؤ]╙╨îخ▒╗âنx╡─╓╚╨ٌ▀`╖┤╨╨ئل╨╬│╔═م╒√╕▓╔w���ثش▀M╢°«a╔·╨┬╡─╖ذ┬╔┬ر╢┤�����ثش╨ك╥ز═╫╔╞╠ى╤a���ث╗╢°╠ط╣ر╝┘╦╫يةت╠ط╣ر┴╙╦╫ي╡─╘ِ╘O����ثش▒M╣▄╩╣╦╞╖╖╕╫ي╡─╥(guذر)╓╞µ£ùl╧ٌ║ٍ╤╙╔هثش╡س╔╨╬┤╨╬│╔╚س┴≈│╠�ةتل]صh(huذتn)╩╜╡─╓▄╤╙╥(guذر)╓╞ةث│²▀\▌¤�����ةت┤µâخ╨╨ئل╡─╥(guذر)╓╞╚╘╥└┘ç╙┌╣▓╖╕╠┴P─ث╩╜═ظ����ثشîخ╙┌╦╞╖╤╨░l(fذة)����ةت┼R┤▓îٌئ�����ةت╒┘╗╪╡╚صh(huذتn)╣إ(jiذخ)┐╔─▄╡─╬ث║خ╨╨ئل╥▓ؤ]╙╨═م╚سىآ╝░�ةث┤╦═ظ����ثشâ╔╫ي╓╨ّز╚ق║╬└و╜ظة░╩╣╙├ة▒ثش╩╟╖ً╙╨╬╬╗╖╕╫ي╓«│╔┴ت╙ض╡╪��ثش╚ق║╬╒J╢ذة░├≈╓زة▒╡╚ûى}╥▓╚╘╚╗┤µ╘┌╥╔┴x���ثش╪╜┤²▀M╥╗▓╜╡─╝أ╓┬│╬╟ف��ةث